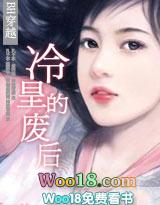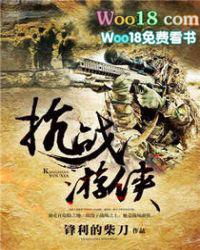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TXT番外全集 > 第864章 轮到溪溪的回合(第5页)
第864章 轮到溪溪的回合(第5页)
,并告诉他:“这封信,我们五年后才会打开。
但只要你记得它存在,你就不是一个人在走。”
傍晚六点,一场小型内部会议在活动室召开。
袁婉青宣布:“下个月,我们要办一场‘跨代对话之夜’,邀请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
每人准备一封信,现场交换,可以选择朗读,也可以私密传递。”
“规则只有一条:不准打断,不准反驳,只能听。”
她说,“听完之后,要不要回应,由你们自己决定。”
林晓彤补充:“我们会提供心理支持小组待命,确保情绪波动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周叶举手:“我可以负责布置场地。
把椅子摆成内外两圈,象征‘靠近’与‘保留空间’的平衡。”
陈默则提议:“用灯光控制氛围。
当一人朗读时,聚光灯只照亮他,其他人隐在柔和的背景光里,减少压力。”
会议结束时,天已全黑。
袁婉青独自留下整理资料,忽然发现信箱里多了一封手写信。
没有署名,只有地址栏写着“致所有曾被遗忘的孩子”
。
她拆开,信纸上有铅笔画的小房子,烟囱冒着烟。
文字稚嫩,像是小学生所写:
>“老师:
>
>我今年九岁,住在城南老纺织厂宿舍。
奶奶说我爸妈不要我了,因为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
可我偷听到她打电话,说他们其实离婚了,谁都不肯要我。
>
>每天晚上我都对着窗户喊‘爸爸妈妈’,可没人回答。
我想写信,可我不敢写‘我想你们’,怕他们更讨厌我。
>
>你们能教我怎么写一封让他们愿意看的信吗?
>
>??一个不想被丢下的小孩”
袁婉青读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她立刻拨通社区教育办的电话,请求调取该片区留守儿童档案。
二十分钟后,她得知那孩子叫王小舟,三年级,成绩中等,长期沉默寡言,已被列为心理关注对象。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林晓彤亲自上门。
开门的是位佝偻老太太,眼神警惕。
“你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