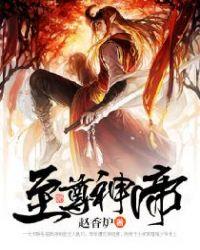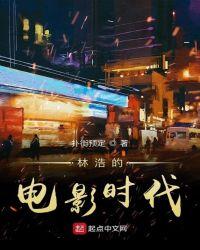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完结TXT精校版 > 第868章 下播之后会干嘛我都不敢想(第1页)
第868章 下播之后会干嘛我都不敢想(第1页)
大年初三,2月18日,一大清早,李珞就从被窝里爬了出来,带着应禅溪和颜竹笙起了床,随后又艰难的把徐有渔从被窝里拉了出来,四个人一起下楼晨跑。
徐有渔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不情愿,但为了应付自家老妈的唠。。。
袁婉青醒来时,晨光已漫过窗台,洒在书桌那本摊开的《声音档案》上。
她梦见了自己小时候住的老屋,墙皮剥落的客厅里,父亲坐在藤椅上看报纸,母亲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作响。
梦里的饭菜香浓得几乎能嗅到,可当她推门进去,灶台却是冷的,锅盖掀开,空无一物。
她站在梦境与现实的交界处,忽然明白??有些家,早已不在原地,却从未真正消失。
她起身洗漱,顺手将王小舟的信折好放进随身包。
今天是“非典型家庭节”
第二次筹备会,也是林晓阳母亲首次参加集体活动的日子。
自从儿子决定调回本地后,老人情绪明显好转,甚至主动提出要为活动做些事。
袁婉青提议她教大家织毛线鞋,像当年给王小舟那样,把温暖一针一线编进生活里。
社区活动中心比往日热闹许多。
志愿者们正忙着布置“记忆回廊”
,墙上挂着几十张泛黄的老照片:有七十年代全家福、九十年代结婚证合影、还有孩子出生时护士抱着拍的第一张照。
每张照片下都附着二维码,扫码即可听到一段语音日记。
一位白发苍苍的父亲说:“我女儿走失那天穿着红裙子,今年春天有人在南方看见一个女人蹲在桥边喂猫,背影像极了她。”
语气平静,却让听者心头沉重。
林晓阳的母亲来得早,怀里抱着一大袋五彩毛线。
她穿了件藏青色针织衫,银发整齐挽成一个髻,眼神温和却不失锐利。
“我想试试。”
她说,“虽然手指不太灵活了,但还能动一天,就想多织一双。”
袁婉青带她到角落的工作台,旁边坐着赵承志,正在誊录一封来自监狱的信。
写信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斗殴致人重伤被判十年,他在信里写道:“妈,你说等我出来你就八十二了。
我不想你等到头发全白,所以每天都在学认字、背法律条文。
我不是想减刑,是怕忘了怎么叫你一声‘娘’。”
赵承志抄到这里,笔尖顿了顿,抬头看见林母,低声问:“您……愿意听听这些孩子的声音吗?”
老人沉默片刻,点点头:“只要他们还想回家,我就愿意听。”
中午饭后,孩子们陆续到来。
“信使小队”
今天任务特殊??他们要帮几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录制“唤醒音频”
。
李锐和唐果一组,负责陪护那位总问“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的老太太。
唐果如今已能断续说话,虽仍羞怯,但在李锐牵手下,竟主动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奶奶,我陪你找儿子。”
录音开始前,袁婉青播放了一段背景音乐??是陈默用老式录音机翻录的一首八十年代民谣,吉他声轻柔如风拂麦田。
老人闭着眼睛,嘴里喃喃:“这歌……我年轻时候常唱……我家门前有棵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