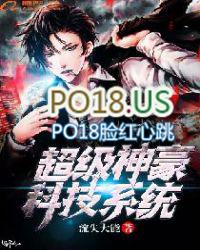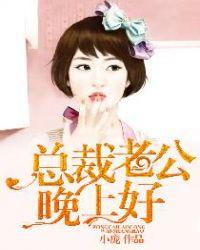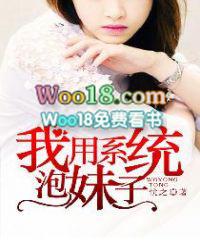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完结TXT精校版 > 第864章 轮到溪溪的回合(第6页)
第864章 轮到溪溪的回合(第6页)
“我们是社区心理援助项目的老师。”
袁婉青出示证件,“听说小舟最近有些心事,我们想陪他聊聊。”
老人犹豫许久,才让开身。
王小舟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画画,听见声音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希望,又迅速低头掩饰。
“小舟,”
袁婉青蹲下与他平视,“我们知道写信很难,尤其是给很久不见的人。
但你知道吗?有时候,信不是为了得到回复,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
男孩抬起头,嘴唇微动。
“我们可以一起写。”
林晓彤温和地说,“不用一开始就写‘我想你们’。
你可以先写‘今天学校发牛奶了,是草莓味的’,或者‘我家楼下那只花猫生了三只小猫’。
一点点来,好吗?”
王小舟终于点头,声音细如蚊呐:“我想……写一句……‘如果你们回来,我会乖乖的。
’”
袁婉青鼻子一酸。
她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恐惧与讨好。
但她没纠正,只是轻轻说:“那我们就这么写。
然后把它放进‘等待信箱’,等哪天他们出现了,就能收到。”
一周后,“信件复活计划”
新增了一个红色信箱,立在活动室外墙边,上面写着:“给尚未归来的人”
。
第一个投信的,正是王小舟。
他踮起脚尖,小心翼翼把信塞进去,回头问:“老师,他们会看到吗?”
“会的。”
袁婉青望着他清澈的眼睛,“只要信还在,希望就在。”
十月末,“跨代对话之夜”
如期举行。
八十平米的活动室坐满了三十四对亲子。
灯光调至微暖,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薰衣草香。
第一位上台的是位六十岁的母亲,她颤抖着展开信纸:
>“儿子,妈当年逼你放弃美术考公务员,是因为怕你饿死。
可你辞职那天离家出走,我才知道,原来精神的饥饿比肚子更难熬……这些年,我偷偷收藏了你大学时画的所有素描。
昨晚我烧了一炷香,对你说:妈错了,回来吧。”
>
>台下,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
接着是一位十七岁女孩,对着父亲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