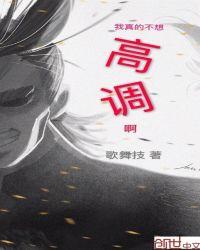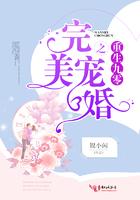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精校版全集 > 第871章 应叔叔那五十只是我用的(第4页)
第871章 应叔叔那五十只是我用的(第4页)
电工证有了,我想再考个社会工作助理资格。
也许……我也能帮别人写一封信。”
李锐在电话那头笑了:“欢迎加入。”
与此同时,袁婉青收到了一封来自边远山区的信。
寄信人是一位支教老师,她说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看了“信纸计划”
的报道后,自发设立了“泥土信箱”
??他们把空罐头盒埋在操场边,每天往里投纸条。
“有个孩子写道:‘我想爸爸回来,但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手机总是打不通。
我把信烧了,烟飘上去,他就能看见吧?’”
袁婉青立即联系公益组织,为那所学校捐赠了一批防水信盒和录音笔。
她还在回信中写道:“你们的泥土信箱很美,因为它贴近大地,就像孩子的思念一样真实。
请告诉那个孩子:烟会散,但我们替他保管这份想念。”
八月十五,中秋夜。
中心举办“月光信笺”
特别活动。
人们在院中摆起长桌,点上蜡烛,写下最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然后投入特制的竹筒信箱。
午夜时分,所有信件被集中焚烧,灰烬随风升腾,如同无数未出口的话语终于飞向星空。
王小舟站在人群中,手里握着一枚铜铃铛。
他把它轻轻放在火堆边缘,看着火焰一点点吞噬线脚,铃声在高温中断响前的最后一瞬,清脆地响了一下。
“奶奶,”
他低声说,“我学会拥抱了。”
唐果则带领孩子们用手语表演《静夜思》。
当最后一个动作落下,全场寂静。
陈默将这场演出录制成无声视频,只保留手部动作的光影轨迹,上传网络后标题为:“有一种思念,不需要声音。”
而就在同一时刻,袁婉青独自走上天台。
她打开手机,翻出妹妹雨晴最后一条短信,发送时间是去世前两小时:“姐,今天阳光真好,我想去海边。”
她仰头望着月亮,轻声说:“雨晴,姐姐带你去看海了。”
第二天,她向团队宣布了一个新计划:“海风邮局”
。
将在沿海小镇设立十个流动信箱,专收“给逝去之人的信”
。
每封信都会由志愿者代为朗读,并录制海浪声作为背景音,回传给寄信人。
“我们要让大海成为传递思念的媒介,”
她说,“因为有些人,再也等不到回信,但他们值得拥有告别的权利。”
项目启动当天,第一封信便来了。
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颤巍巍地递上一个泛黄的信封,里面是一张五十多年前的情书草稿,从未寄出。
“我爱人去年走了,”
她说,“我们年轻时相爱,可家里反对,我没勇气坚持。
现在我想告诉他,我这一生,只爱过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