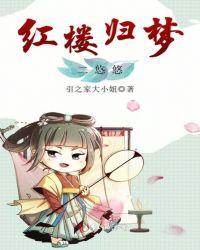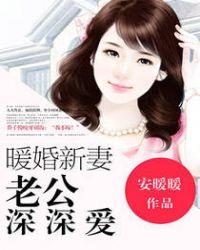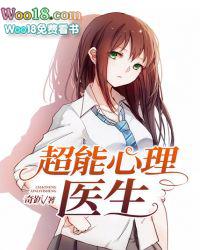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未删减完整版TXT > 第871章 应叔叔那五十只是我用的(第3页)
第871章 应叔叔那五十只是我用的(第3页)
原来,他的儿子早在十年前就因吸毒overdose离世。
那时他正忙着破案,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事后他把儿子的照片锁进抽屉,再也不提。
这些年,他拼命工作,帮别人找回孩子,其实是想把自己那份遗憾,一点点补回来。
“我以为我不配当爹,所以我就当别人的‘临时父亲’。”
他说,“可我现在才明白,原谅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放下的。”
三天后,他执意出院,回到中心。
护士劝不住,只好带着药箱随行。
他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次“极速响应队”
培训教案,并亲手交给阿杰。
“记住,救人不只是抢时间,更是抢人心。”
他说,“有些人表面冷静,其实心里早就塌了。
你要做的,不是让他们坚强,是让他们敢软弱。”
七月流火,城市迎来最热的一段日子。
一场名为“听见沉默”
的巡回展览正式启动,首站设在市图书馆。
展厅中央,是一堵由上千封匿名信拼成的“声音墙”
,每一封信都附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后可听到志愿者朗读的音频。
周志远也被邀请来参加开幕仪式。
他站在人群中,看着墙上自己的那封信被放大展出,旁边播放着他母亲那段颤抖的录音:“志远,妈今天煮了红豆汤,多加了一勺糖,等你回来喝。”
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这时,一个小女孩跑过来,仰头看他:“叔叔,你是信里的哥哥吗?”
周志远点头。
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红豆,认真地说:“这是我昨天攒的。
妈妈说,每一颗豆子都代表一句没说出来的话。
我把这颗送给你,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喝到甜汤。”
他蹲下来,接过豆子,轻轻放进胸口的口袋里。
“谢谢。”
他说,“我会的。”
展览第三天,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他是当年劳教所的旧职工,认出了周志远。
“小伙子,我记得你。”
他说,“那时候你总一个人坐在操场角落看书。
别人笑你装文化人,可你说:‘我要让我妈觉得,她的儿子没给她丢脸。
’”
周志远怔住了。
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但此刻听起来,竟如此真实。
老人拍拍他的肩:“你现在做到了。”
那天晚上,周志远第一次主动拨通了李锐的电话:“我想报名成人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