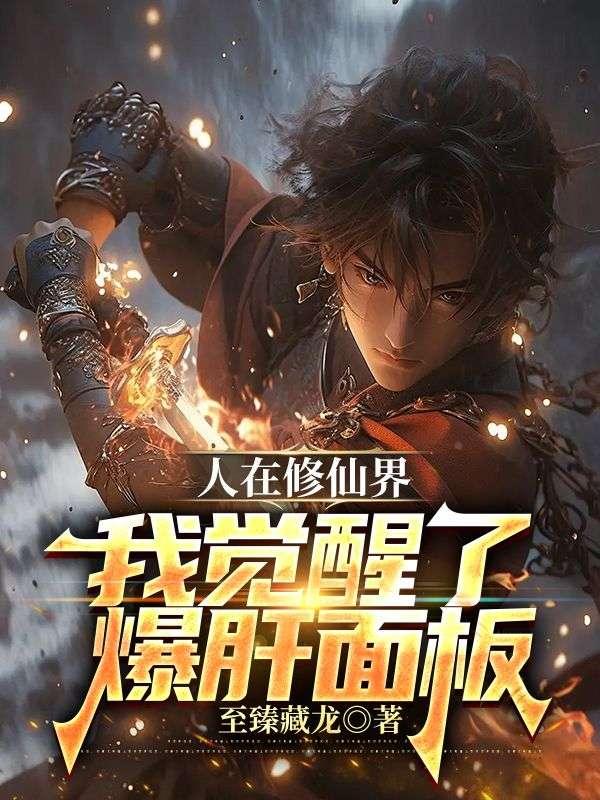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TXT完整无错版 > 第861章 把老丈人们都绑上战车(第3页)
第861章 把老丈人们都绑上战车(第3页)
爸爸不能陪你吹蜡烛,但我给你唱首歌吧……”
歌声沙哑而笨拙,唱到一半便停住了,只剩沉重的呼吸声。
他摘下耳机,眼眶红了。
“那时候还不敢说完一句话。”
他低声说,“现在想想,真是傻。”
周叶握住他的手:“可我还是听见了。”
展览结束前,袁婉青宣布了一个消息:“‘青春纸船’即将启动‘回声计划’??我们将邀请曾经接受帮助的家庭成员,成为新一期课程的分享嘉宾。
他们不再只是倾听者,也可以是讲述者。”
台下掌声雷动。
一周后的周三傍晚,袁婉青接到陈默电话。
他的声音有些异样:“老师,我爸……今天叫我‘小默然’了。”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然后呢?”
“我愣住了。”
陈默说,“十年没人这么叫过我。
我以为我会反感,可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先出来了。
他就站在我面前,端着一碗热汤,叫我‘小默然,趁热喝’。”
“那你喝了没?”
“喝了。”
他顿了顿,“我还叫了他一声‘爸’。
声音很小,但他听见了。
他手抖了一下,差点把碗打翻。”
袁婉青靠在窗边,望着天边渐沉的夕阳,轻声说:“你看,名字是有魔力的。
它能把散落的灵魂,一点点唤回来。”
七月的第一天,气温突破三十八度。
城市像蒸笼一般闷热,连风都带着灼意。
然而这一天,“青春纸船”
迎来了最热闹的一期活动??“家庭开放日”
。
林母术后恢复良好,特意穿了一条碎花连衣裙出席;周海生带来了自家腌的梅干菜,说是“给闺女改善伙食”
;陈父则默默坐在角落,手里攥着一本旧相册,时不时翻看一眼。
孩子们带来了亲手制作的小礼物:一幅画、一首诗、一段录音,或是一只折得不太标准的纸船。
老人们接过时,手指微颤,眼里泛光。
袁婉青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欢声笑语,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
她曾以为治愈是缓慢而孤独的过程,可此刻她明白,真正的疗愈,发生在彼此凝视的眼神里,发生在颤抖的拥抱中,发生在那一声迟来的“爸”
“妈”
“女儿”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