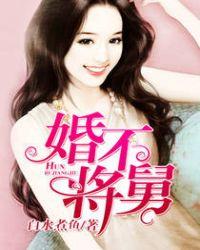宝书网>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32章 江南消息(第2页)
第132章 江南消息(第2页)
良久,他起身走进地窖,取出一尊铜铃??那是多年前一位母亲亲手交给他,内壁刻着她儿子的名字与被捕日期。
他将铃悬于老槐枝头,又取笔蘸朱砂,在铃下木牌写上:“**林照,三十六岁,教师,以诗育人,以命守道。
**”
铃随风轻晃,发出一声悠远的鸣响,如同回应。
周念看着,忽然跪下,从怀中掏出一本薄册,双手奉上:“这是我在旅途中写的《亡名考》,共十卷。
我不敢称史,只愿做一块砖石,垫在后来人脚下。”
阿启接过,翻开第一页,只见开篇写道:
>“所谓历史,并非帝王将相之履历,亦非胜利者之颂歌。
它是无数普通人挣扎求存的痕迹,是母亲临终前对子女低语的真实,是孩子在寒夜里记住的一句诗,是一个名字在百年后仍被人呼唤的回音。
>我辈所做之事,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中打捞沉船,哪怕只能拾起一片碎瓷,也要让它映出昔日的光。”
阿启合上书册,轻轻搁在一旁,然后握住周念的手臂,将他扶起。
“你已不必再跪。”
他说,“你们这一代,生来就该站着说话。”
午后,馆外传来喧闹声。
一群年轻人簇拥着一辆牛车驶入院门,车上堆满陶片、石板、铜牌,皆来自各地民众自发送来的纪念物。
有位戴眼镜的女孩跳下车,高声道:“我们是‘寻名协会’的学生!
这趟跑了六个省,收了两千多件铭文,全都按地域分类好了!”
她话音未落,另一人推开人群进来,竟是当年博物馆读书会上那个画梦的小男孩。
如今已是少年,脖子上仍挂着阿启赠予的铜片“听”
。
他手里捧着一幅新画:画面中央是一条大河,河床由无数名字铺成,两岸灯火通明,人们站在桥上向下投灯,光点落入水中,化作游动的文字鱼群。
“我又梦见您了。”
他说,“这次您不在高塔下,而在河中央的一艘船上,撑篙前行。
您回头对我们说:‘跟上来,水不会淹死记得的人。
’”
阿启接过画,眼中微热。
他将画挂在《众声录》手稿旁,与前一幅并列而置。
当晚,众人齐聚地窖,举行一场非正式的“归名仪式”
。
三百七十二个名字逐一被读出,每念一个,便有一人点亮一盏油灯,置于环形碑墙的凹槽之中。
灯光渐次亮起,宛如星河流转。
当最后一个名字落下??“苏婉儿,十九岁,护士,因私藏病患记录遭拘押,死于寒冬暴雪夜”
??全场寂静无声,唯有烛火噼啪作响。
阿启起身,走向中央石台,取出《草芥录?终章》,将其轻轻放入一只陶瓮中,封口,再以红泥加盖印玺。
“这本书完成了它的使命。”
他说,“它曾是黑暗中的低语,是逃亡路上的秘密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