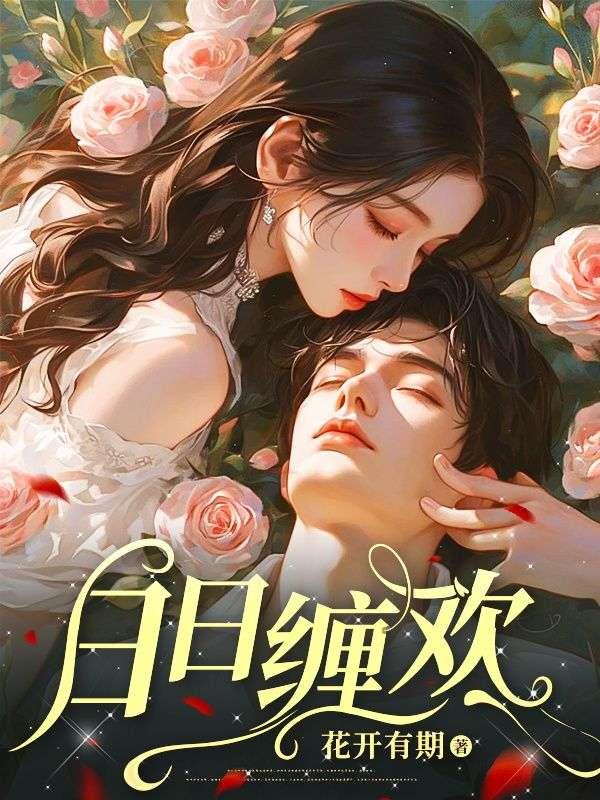宝书网>复仇之宿敌追着我哄 > 欲局乱一(第1页)
欲局乱一(第1页)
除个别特殊的部门外,大家都进入了一种放松的状态,沈妆幕这几日忙得团团转,连跟余鸿凝聚一聚的时间也没有,但也奇怪,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找沈妝幕了。
自那日放出萧仲的消息,沈妆幕专门去宫里打了照面,为萧含凨寻了个居住的好地方,派一些人远远保护着她。如今这件事风头还没过去,余鸿凝暂时挪不得。
只是近几日听皇帝说太子终于想通,开始对政事上手了,这事儿沈妆幕不敢苟同。别的不了解,但她表哥心系百姓,如果心思肯往政事上学,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
况且,皇帝虽然佳丽三千,孩子却只有这两个。粟朝也在这个时候向峮国赠送典礼,恭顺亲好。
本以为一切安定,却在她下职后收到赵熠约她去世子府的消息,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沈妆幕专门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里面套着月白色夹袄,下身青色织金纹百迭裙,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白大氅,脸上扑了淡妆,于白雪中莹莹地一个妙人。
沈妆幕在婢女的搀扶下上了马车,隐隐的笑意爬上脸颊,这是她跟赵熠认识的第一个年,也是她中毒之后正儿八经能过的一个年。
这对沈妆幕来说似乎是个节点,用来宣告她之前的病痛全都过去了,如今她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她舅舅为什么要在她娘事情瞒着她,反正当年的真相已经昭告天下。
马车的车辙声渐小,缓缓停下。沈妆幕下着马车的梯子,抬起头却看到赵熠裹着大氅,负手而立。
深色的长衣将他衬的深沉稳重,琢磨不透。可在沈妆幕的眼里,他就像黑夜里的月,皎洁明亮,为她排忧解难,顶着被她误解的风险也要保护她。
赵熠在她下来的一刻就向她走过来,看到她微笑的眉眼,不由问:“你笑什么?”
“因为看见你了。”她笑的更加灿烈。
陡然的一句话,说的赵熠愣了一会儿子,被沈妆幕拉着往府里走才后知后觉的笑出声,方才的紧绷在此刻都舒展开来。
“你别逗我了。”他笑着捂住了眼睛,薄红从脖子蔓延到了耳稍,连脸颊也是红红的,久久不曾散去。
这幅样子惹得沈妆幕连连看他,总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终是没回答。
二人进了正厅,温暖的热气扑面而来,头发丝儿上挂着晶莹的水珠,赵熠手里拿着帕子,弯腰从她发丝儿上捋着擦拭。
把大氅脱下下,手里各端着一碗不断窜涌热气的茶,手指尖儿的麻木被炙热的茶杯一点点的侵蚀,不一会儿就暖呼呼的了。
“你此次邀我来,可是有要事?”沈妆幕即便欣喜他在门口等自己,也还是没忘了他苦大仇深的样子。
“你不说我都忘了。”赵熠走了几步坐到沈妆幕旁边,认真的观察着她的眉毛眼睛,又移开眼,独自思衬着要不要宣之于口。
“有什么不能讲的?”沈妆幕看不得人犹犹豫豫的,明明是把她约来了,却还在想着能不能说。
“你记不记得前几个月把我捅伤的那个小孩儿?”见沈妆幕还没想起来,又道:“穿的一身花花绿绿,走起路来叮当响的那个。”
她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点了点头。赵熠继续道:“他就是苗缰人,我当年将他带出来,已经八岁左右了。”
“他父亲是苗疆人的族长,只有他一个孩子,苗疆传统乃是传女不传男,就把他当成女孩儿来养了。他从懂事起就学苗疆的蛊毒,不说万蛊可解,但认识蛊,还是很轻松的。”
他一连说了这一大堆,沈妆幕敏感的认为这堆话一定跟自己有关系。自从他们两个有意开始,赵熠跟她说话从不会绕弯,除非怕她接受不了。
一个危险的想法在沈妆幕心底浮现,不由悠悠地往下沉,脸色都变了。
“没事,你别慌。”赵熠一下子攥住她的手,“我是想问你,陛下有没有跟你说你中了什么毒?”
接着他从胸前的衣服里掏出一个纸条,纸条的边缘已经模糊了,可见纸张的质量着实不太好。
他在两人眼皮底下打开,只见淡黄色的纸面上,写着“沈姑娘中的是蛊。”
其中“蛊”这个字,被刻意写大并且描粗了一些。
字体并不好看,窝成一团,可一瞥一捺又刻意的拉伸开,显得滑稽十分。
“蛊?”
“蛊可引,毒可解。”赵熠将纸条递给她,观察着她的神情,幸好更多的是茫然而不是绝望。
“舅舅并未明说我所中何毒……”她脑海里浮现曾经在昏暗狭窄的屋子里,一个人凭着意志撑过寸寸断骨之痛的情景。四肢百骸间隐痛阵阵,不由屏住呼吸。
“妆幕?”
她正出神间被赵熠叫醒,堪堪稳住心神,道:“我想着反正没希望了,就没多问。”
“别灰心,不到最后一步不能放弃。”赵熠眼中的坚定被她看在眼里,可她的身体状况她自己清楚,笑了一下也没反驳他。
“妆幕。”赵熠忽然颁过她的肩膀,看着她道:“苗疆像样的巫师在几年前就被我一锅端了,陛下去哪里为你寻的医师?”
“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