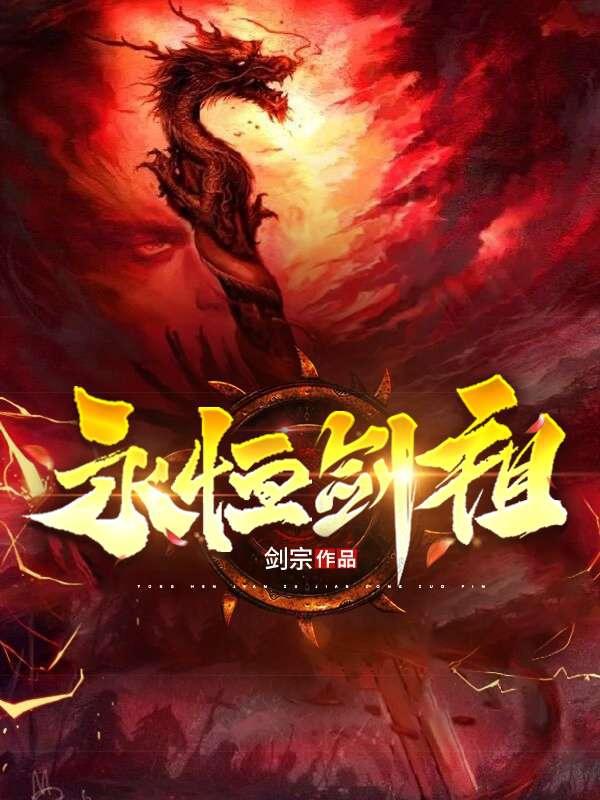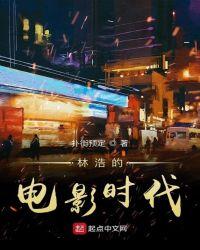宝书网>女帝,从招聘诸葛亮开始 > 100110(第3页)
100110(第3页)
杨氏坐在一旁,手里缝补着一件旧衣,针线在布料间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又低头继续手上的活计,轻声道:“快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呢。”
宗武撅了撅嘴,显然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但终究抵不过困意,眼皮渐渐沉了下来。他的小手仍攥着被角,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要是每天都能吃上这个面就好了……”
杨氏听了,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唇角浮起一丝苦笑。她何尝不想让孩子们顿顿吃饱?可这世道,能活下来已是万幸。
杜甫望着熟睡的儿子,目光深沉。
他想起天宝年间的长安,那时他还年轻,也曾意气风发,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满腹诗书,总能谋得一官半职,让妻儿过上好日子。可如今,他漂泊半生,落得个“饥走荒山道”的境地,连一顿饱饭都要靠他人接济。
“若是太平盛世……”他低喃着,却又止住了话头。
这世上,哪有什么若是?
窗外,一阵夜风掠过,吹得院中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几片枯叶被卷起,轻轻拍打在窗棂上,像是某种无言的叹息。
杨氏放下针线,轻声道:“你也早点歇着吧。”
杜甫点点头,却没有动。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孩子们的脸上——宗文已经睡熟,呼吸均匀,而宗武的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仿佛梦里还在回味那碗面的滋味。
良久,他低声道:“若是天下百姓都能吃上一碗热面,该多好。”
杨氏没有逃避,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道:“若是你说的仙人是真的,那天下的百姓肯定不会再受饥寒交迫之苦。”
杨氏的话语像一粒火星,倏地点亮了杜甫浑浊的眸子。
夜风掠过窗棂,杜甫的思绪忽而飘回天宝三载。
那时秋深露重,他与李白、高适三人醉卧石阶,仰观星河,一起寻仙。
李白解下腰间美酒狂饮,高适击剑而歌,而他——尚是裘马轻狂的少年郎,袖中藏着新作的《望岳》,自以为笔下可擎天地。
“寻仙去!”李白忽地翻身坐起,玉冠斜坠,眸中映着月色,如剑光凛冽,“访道嵩山,乘鸾跨鹤,岂不快哉?”
高适大笑,剑穗在夜风中飞扬:“李十二又发癫了!”
说罢,便跟随着李白的脚步大步迈去。
杜甫在后看着这一幕,微微一笑,也跟了上去。
三人策马上嵩山时,正值云海翻涌。李白一袭白衣在前引路,袖袍灌满山风,恍若真要羽化登仙。
“杜二!”他在雾中回首,笑声清越,“若遇真仙,我为你讨颗金丹,治治你这愁眉!”
年少的杜甫眉峰黑浓,天生一副忧思之相。他自幼“嫉恶怀刚肠”,见不得世间不平事,故而眉间常凝着郁色。可此时的他尚未历经乱世,仍是那个裘马轻狂的少年郎,胸中意气未减分毫。
他扬鞭催马,朗声应道:
“若是真遇真仙,我要求上千万颗金丹!”
“一颗治贪官污吏,一颗救黎民饥寒,一颗平边关战火,其余的就用来还天下太平!”
他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惊起几只栖鸟。李白闻言大笑,袖中掷来一壶酒:
“好志气!饮了这杯,今日定要替你寻个神仙来!”
高适在后头气喘吁吁,他的马不如李白的骏逸,也不似杜甫的灵
巧,驮着他这“老骨头”(其实不过三十余岁)艰难攀行。
“十二郎!杜二!你们慢些!”
“爹?”
宗武的梦呓将杜甫惊醒。
窗外仍是漆黑一片,没有嵩山云海,没有太白高适,只有远处森森夜色。
杜甫摩挲着手中想李白写的诗稿,忽然想到——
那日下山时,夕阳将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白醉醺醺地挂在马背上,哼着无人听懂的曲调。高适的衣衫沾满泥点,对着杜甫摇头苦笑,今天又是没有寻到仙人的一天。
现在想来,那是一段很好的时光。
不似今日。
李白成了谪仙人,却困于人间;高适拜将封侯,终难救乱世;而他自己,从裘马轻狂的少年,熬成了“白头搔更短”的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