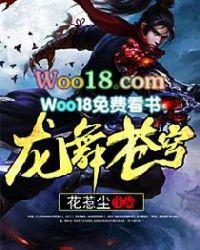宝书网>二婚嫁京圈大佬,前夫气疯了 > 第300章(第1页)
第300章(第1页)
许知意没有反驳,只是平静地调出另一份数据模型:“这是我根据新方案做的计算机模拟,成功率预测在92%以上。数据不会说谎,我们可以用实验来验证。”
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强迫,却带着一种基于绝对专业和海量知识储备的自信,让人无法辩驳。
刘教授将手里的文献放下,看着白板上那个精准的结构图,最终长出了一口气,对王工说:“就按许组长的方案,马上准备实验!”
实验室的灯,再次彻夜通明。
但这一次,空气中不再是沉闷和焦虑,而是被重新点燃的希望。
结果在不到三天后就出来了。
当全新的数据曲线图生成在电脑屏幕上时,整个实验室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那条代表着S-3A激酶活性的曲线,平稳得像一根水平线,在72小时的观测点上,活性维持率高达98,7%!
一个质的飞跃!
“天呐!成功了!真的成功了!”王工激动地
挥舞着拳头,眼眶都红了。
所有人都望向许知意,眼神里充满了敬佩,甚至是崇拜。
这个年轻得过分的孕妇,用一次天才般的洞察,解决了困扰顶尖团队数周的死结。
她不仅仅是项目的名义负责人,更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技术核心。
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一个更严峻的挑战便接踵而至。
院长亲自打来电话,语气兴奋中带着一丝凝重。
医院收到了国家级生物医药创新竞赛的正式邀请,这是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最高殿堂。
院里决定,将许知意团队的项目作为今年的王牌推上去。
但提交初步成果的截止日期,是一个月后。
更要命的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在业内流传:秘密实验室也在进行同类靶向药的研发,并且据传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时间,一下子成了最宝贵的资源。
许知意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穿梭的人流,眉头紧锁。
一个月,要拿出足以在国家级竞赛上亮相、并能与国际巨头抗衡的成果,常规的研发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下午的紧急会议上,她宣布:“启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辅助筛选技术,对药物靶点进行高通量筛选和验证。”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这项技术是前沿中的前沿,虽然高效,但风险极高,对操作的精确度和生物伦理的把握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一旦出现脱靶效应,整个实验数据都可能作废,甚至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此前,因为风险过高,这个方案一直被搁置。
“许组长,这太冒险了!”
刘教授第一个表示担忧,“我们好不容易才稳定了激酶,现在上基因编辑,万一……”
“没有万一。”
许知意打断了他,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风险我评估过。时间不等人,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辉瑞不会等我们,竞赛的截稿日期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