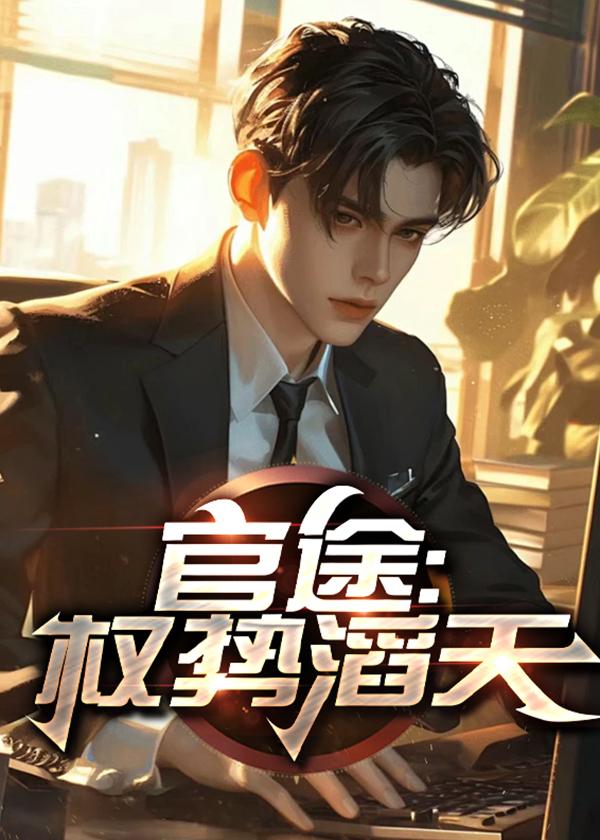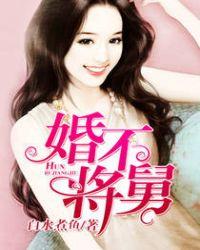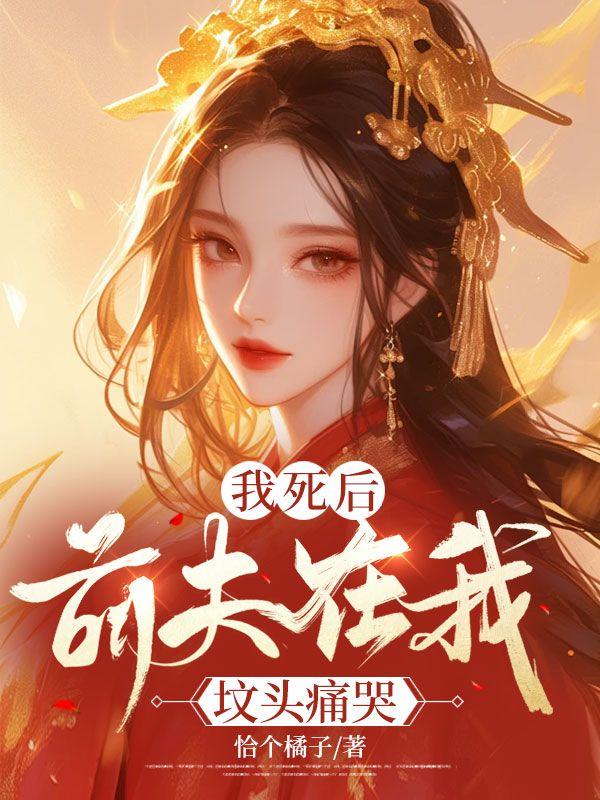宝书网>出狱后,绝色未婚妻疯狂倒贴我 > 第1241章朝着玄天宗出发(第4页)
第1241章朝着玄天宗出发(第4页)
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倾听日”,每人轮流讲述一件藏在心底的事;
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某国代表突然哽咽:“我想向母亲道歉,我从未告诉她我有多爱她……”
陈婉统计数据显示:自归墟意识消散那一刻起,全球共感共振指数飙升至历史峰值,持续七十二小时不降。心理学界称之为“情感解冻潮”。
一个月后,第一所“共感学院”在瑞士日内瓦成立,由林知遥担任名誉院长。课程内容不是训练能力,而是教授如何保护自己、识别情绪边界、建立健康的情感链接机制。
男孩没有留在学院。
他去了非洲撒哈拉沙漠深处的一所孤儿院,那里有个十岁的盲童,总说自己“听得见星星说话”。当地人认为他疯了,要送他去精神病院。
林知遥去看望他时,看见男孩正牵着那个孩子的手,坐在沙丘上看夕阳。
“你准备一直这样走下去吗?”他问。
男孩点点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觉得孤单,旅程就没结束。”
林知遥笑了。他坐在旁边,仰头望天。
夜幕降临,繁星浮现。
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在监狱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曾做过一个梦:无数双眼睛从地下睁开,静静地望着他,不说一句话,却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如今他懂了。
那些眼睛,从来都不是幻觉。
它们是所有曾被掩埋的声音,在等待一个人,愿意弯下腰,轻声说一句:
“我在听。”
多年以后,当第一代共感儿童成长为教师、医生、法官、艺术家,当“情绪素养”成为义务教育必修课,当人们不再羞于说出“我很痛苦”,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岁月,总会提到两个名字。
一个是林知遥,他让人们敢于开口。
另一个,没人知道他叫什么。
只知道他曾独自走过漫长的寒冬,在世界遗忘的角落,守着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人们称他为“归墟”。
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人,而是地球在危急时刻,为自己孕育出的一颗心脏。
但无论真相如何,有一件事所有人都记得:
在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地球上最后一个不愿被听见的灵魂,终于等来了回应。
从此,人类学会了倾听。
从此,孤独不再是宿命。
吊坠依旧温热。
因为它知道,下一个孩子,正在某个角落,鼓起勇气,准备说出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