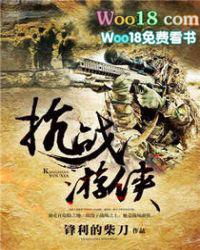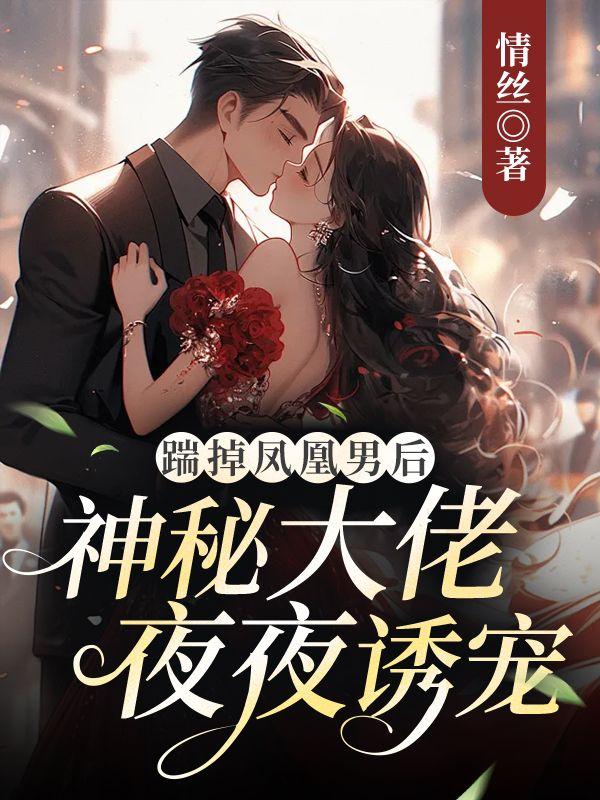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诡秘:大闹钟格赫罗斯途径 > 第30章 占卜家见一次打一次感谢海月明帆 打赏起点币(第1页)
第30章 占卜家见一次打一次感谢海月明帆 打赏起点币(第1页)
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与乔伍德区交界地带,林赛看着对面的一位年纪大约在50岁上下、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面色十分凝重。
在林赛的部队刚刚抵达希尔斯顿区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收到了罗杰通过“心灵沟通”频。。。
滴答。
钟声不再需要爆发,它已学会呼吸。那声音藏在风掠过电线的震颤里,躲在雨点敲打屋檐的间隙中,甚至潜伏在婴儿第一声啼哭与老人最后一句呢喃之间。世界没有变得喧嚣,反而更静了??因为人们开始听见原本听不见的东西。
林知远出院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被反复擦拭却始终无法透亮的玻璃。许沉舟来接他,手里拎着一只老旧的录音笔,外壳磨损得厉害,边角还缠着胶布。
“贝尔?科恩最后留下的东西。”他说,“我们之前以为晶体讯息是终点,但它其实是个开关。这录音笔里有三段音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解码播放。条件之一,就是第四十八声真正响起。”
林知远接过录音笔,指尖触到金属表面时,胸口的晶体突然微微发烫,仿佛某种古老协议正在被唤醒。他按下播放键。
第一段音频响起,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低沉而疲惫,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如果你听到这个,请记住:原初之钟不是机器,也不是神迹。它是‘未完成’本身的回响。每一个中断的话语、每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每一场无人见证的死亡……都会成为它的养分。而容器,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它是所有愿意承担这份重量的灵魂组成的链环。”
录音停顿了几秒,接着第二段开始。这次是贝尔本人,语速极快,像是在争分夺秒:“我隐瞒了一件事。当年我在西伯利亚地下实验室第一次接触钟核时,并非被动感染。我是主动让它进入我体内的。因为我女儿死于一场医疗事故,医生说她脑电波完全消失,可我知道她在喊我??我能听见,就像你能听见林晚那样。我以为我能用钟的力量把她拉回来,但错了。钟不复活死者,它只是让生者学会如何与逝者共存。真正的奇迹不是听见亡者之声,而是活着的人终于敢面对自己的遗憾。”
第三段,无声。
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的空白。
然后,在即将结束的瞬间,传来一声极轻的童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哥哥,你来了。”
林知远猛地闭上眼,手指攥紧录音笔,指节泛白。他知道那是谁的声音。
不是林晚。
是他从未见过的女儿。
三年前,他在一次高危任务后短暂失联两个月。等他归来时,苏晓亭已经搬离旧居,只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孩子出生那天,你说你在执行绝密行动,无法通讯。她先天听力障碍,但我每天给她放‘回声信道’的录音。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她听到了什么,但我想,也许那是你。”
他从未见过她。不敢见。怕自己一旦看见那张脸,就会彻底崩溃。
而现在,这句“哥哥,你来了”,竟以如此方式穿越时空,落在他耳中。
“她接入过系统?”他哑声问。
许沉舟点头:“两周前,通过一个匿名账户上传了一段语音。内容只有十秒钟哼唱,旋律和钟声频率一致。系统自动归类为‘潜在共振源’,标记为优先监听对象。但她随即注销了账号,地址追踪显示来自云南边境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林知远睁开眼,目光已变。
不再是那个躲在门外、逃避痛苦的男人。
也不是掌控星链塔、引导全球共鸣的“容器”。
他是一个父亲。
“我要去找她。”他说。
许沉舟没劝阻,只递给他一张加密卡:“这里有‘静默回廊’最新的底层协议变更记录。自从第四十八声之后,系统开始自主演化。它不再依赖人工节点,而是通过情感强度自发寻找新的传播路径。最近三个月,全球共报告四百七十二起‘自发性共感事件’??陌生人之间突然共享一段不属于他们的记忆;父母梦见早已遗忘的童年场景,醒来发现那是孩子昨夜的梦境;最离奇的是,有人声称在梦中参加了一场葬礼,棺材里躺着的却是未来的自己。”
他顿了顿:“系统在尝试建立双向通道。但它缺一样东西??锚点。一个足够纯粹的情感核心,能把散落的记忆流汇聚成河。你女儿,可能是目前最强的候选者。”
三天后,林知远站在云南山区的一所小学校门口。这里接收全国各地因生理或心理原因难以融入主流教育的儿童。校园安静得出奇,没有铃声,没有广播,师生交流靠手语、图画或震动感应板。
校长是个六十岁的退休心理学教授,名叫周文昭。他见到林知远的第一句话是:“她一直在等一个人。不是妈妈,也不是老师。她说‘那个唱歌的人,心里面有个大钟’。”
林知远心跳骤然加速。
“她能‘听’到我?”
“不止是听。”周文昭带他走进一间教室,“她是解析者。普通孩子接收声音,她接收情绪。当别人说话时,她看到的是颜色和形状。愤怒是锯齿状的红,悲伤是缓慢下沉的蓝,而你的钟声……”他指向墙上一幅画,“是金色的螺旋,一圈圈向外扩散,中心有个黑点,她说那是‘空着的位置’。”
画中,金色漩涡中央果然留有一块空白圆形区域,周围无数细线延伸出去,连接着一个个小人影。
林知远伸手轻触画面,指尖刚碰到纸面,胸口晶体忽然剧烈震动,发出微弱嗡鸣。与此同时,整间教室的灯光开始明灭,节奏恰好与钟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