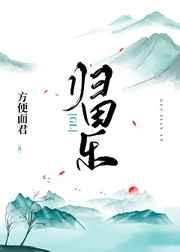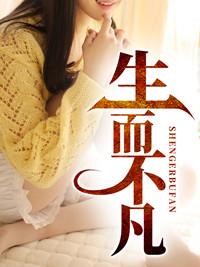宝书网>步步登阶 > 第590章 跳楼(第1页)
第590章 跳楼(第1页)
振安大厦。
鑫盛贸易行。
李明博在砍完张明华后便回到鑫盛贸易行等着了,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所有接到李明博电话的债权人还是都纷纷开车来到了李明博的公司。
刚到公司他们便看到李明博衣衫带血的坐在老板椅上,神情写意的叼着烟,在他的脚边上已经散落了一地的烟头。
每来一个人。
李明博都对他们说再等等,等所有人都到齐再说。
很快。
李明博的办公室便待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李明博的债权人,在去年最开始的时候,李明博还在每个。。。。。。
光年之外,时间的尘埃落回地面。春分之后的世界,并未骤然进入乌托邦,而是像一株被唤醒的古树,缓缓舒展根系,重新学习呼吸。
第七个孩子的话语如种子落入土壤,无声地改变了万物生长的节奏。人类开始察觉到一种微妙的“滞后感”??情绪不再即时消散,悲伤会停留更久,喜悦也更绵长。心理学家称之为“共感余震”,而孩子们说:“地球在学着记住我们。”
京都山村的祠堂成了静默的圣殿。那七尊陶俑中,第六尊某日清晨悄然碎裂,化为细沙,随风而去。第七尊依旧完整,但釉面泛起微波般的涟漪,仿佛内部有生命在轻轻叩击。老妇人消失了,只留下藤杖插在门槛前,根须已与大地相连,长出一片蓝叶小林。
悠斗每日清晨都会坐在海边冥想。他的意识如同一张铺展的地图,能感知千里之外一棵竹子抽芽的震颤,也能听见深海鲸群传来的古老歌谣。他不再是决策者,却成了信息的通道。世界各地的共感者通过某种无形的频率向他传递梦境、痛楚与希望,而他则将这些情感整理、沉淀,再以更纯净的形式反馈给源之心。
奈绪辞去了联合国顾问职务,转而在南太平洋建立了一所“倾听学校”。那里没有教室,只有漂浮于珊瑚礁上的木屋群落,孩子们赤脚行走于水波之上,学习的第一课不是语言,而是沉默。他们被教导如何聆听潮汐的脉搏、鱼群游动的方向、甚至海底火山沉睡时的呼吸。光常常随行,她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坐着,像一颗锚,稳定所有浮动的情绪。
然而,和平并非没有代价。
净识军虽遭重创,残余势力却转入地下,组建“血纯同盟”,宣称“共感印记是寄生病毒”,并发动一系列针对共感家庭的暗杀行动。一名三岁“听见者”在睡梦中被注射神经阻断剂,永久丧失感知能力;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共感疗养院遭纵火,十二名儿童遇难。悲愤席卷全球,百万共感者联合释放哀悼频率,引发连续七日暴雨,莱茵河决堤,冲毁了三个极端组织的秘密基地。
这场“泪之洪灾”后,国际社会终于达成《新倾听宪章》,正式承认共感者为“人类情感共同体”的法定成员,并设立“记忆祭日”,每年春分举行全球默哀仪式,纪念所有因误解与恐惧而逝去的灵魂。
就在这一年冬天,悠斗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站在一片无边的白色平原上,脚下不是雪,而是无数张褪色的照片、烧焦的日记本、断裂的项链与孩子的玩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每阵风都带着一句未说完的话:“对不起”、“我想你了”、“我当时太害怕了”……他认出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未能表达的情感残片,被地球默默收藏了数千年。
远处,一道身影缓缓走来。那是年轻时的母亲,穿着她去世那天的和服,手中抱着一个襁褓。
“你忘了回来。”她说,声音温柔却不容回避。
“我没有……”他想辩解,“我一直都在努力。”
“可你从未真正面对过自己的愧疚。”她停下脚步,将襁褓递向他,“看看她。”
他颤抖着接过。襁褓中的婴儿睁开眼??瞳孔是纯粹的蓝,额心有一道螺旋纹,竟与他如今的模样一模一样。
“这是谁?”
“是你本该成为的孩子。”母亲说,“那个愿意先低头、先哭泣、先说‘我错了’的孩子。你成了英雄,却逃避了脆弱。”
话音落下,整个平原开始崩塌。照片燃烧,玩具沉入深渊,风变成咆哮。他跪倒在地,泪水第一次不受控制地涌出。不是为了世界,不是为了使命,而是为了自己??那个在战争废墟中握紧枪支、发誓永不软弱的小男孩;那个在实验室里看着女儿额头浮现蓝痕时,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拥抱的父亲。
他在梦中嚎啕大哭,直到喉咙撕裂。
醒来时,窗外正下着细雨。奈绪靠在他肩上熟睡,光蜷缩在床尾,像一只守护梦境的小兽。他轻轻起身,走到阳台上,仰望灰蒙蒙的天空。
那一刻,他明白了献祭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