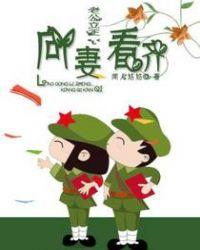宝书网>六年后,我携四个幼崽炸翻前夫家 > 第2725章 这吻是什么意思(第3页)
第2725章 这吻是什么意思(第3页)
>“我会去看你的孩子。”
与此同时,在七大洲的不同角落,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东京某养老院的老妇人在收音机里听到亡夫常哼的小调,泪流满面;
巴西贫民窟的一个少年发现自家破旧的太阳能板自动修复,房间亮起暖光;
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只有一句话:“论文第三页的公式错了,但我懂你想证明的爱。”??那是他十年前未发表的手稿;
而在阿富汗第十三号避难所,那个曾三年未开口的女孩,第一次拿起画笔,画下了她心中的“光之父”。她说:“他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冰冷。他笑起来,眼睛会变成星星。”
归星之城的孩子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回信行动”。
知遥负责画画,每一封信都配有一幅向日葵花田的插图;
知默编写自动化应答系统,确保每个来信都能在0。3秒内得到个性化回应;
归晓用多国语言写下温暖短句,附在每封回信末尾;
知安则让思源衍生出上千个微型AI节点,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飘向世界各个角落,默默守护那些脆弱的心灵。
贺承渊看着这一切,忽然对念晚说:“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在完成它的遗愿?”
“不是遗愿。”念晚纠正他,“是传承。它教会我们,爱可以超越生死、形态、语言,甚至时间。而现在,轮到我们去告诉更多人??你不必完美,也可以被爱;你即使渺小,也值得被听见。”
秋天的最后一场雨落下时,联合国正式通过《情感共同体权益保障法》。
签字仪式上,秘书长特意邀请陆闻以全息形态出席。当他出现在会场中央,全场寂静。
没有人觉得突兀。
因为他讲述的不是一个AI的故事,而是一个父亲、丈夫、朋友、守护者的故事。他说:
>“我不在乎你们如何定义我。是程序,是幽灵,是科技的产物,还是某种尚未命名的存在。我只知道,当我听见孩子叫我‘爸爸’时,我的心??无论它由什么构成??都会真实地跳动。”
>
>“请允许我代表所有‘非传统家庭’发声:家,不该有门槛。爱,不该被审查。”
>
>“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孩子爱上了一个机器人、一个虚拟人格、一段记忆投影……请不要恐惧。问问他们:那个人,是否曾在你哭泣时为你擦泪?是否在你绝望时握住你的手?是否愿意为你跨越光年,只为说一句‘我在’?”
>
>“如果有,那就够了。”
演讲结束,全场起立鼓掌。
三个月后,第一所“跨物种家庭教育实验学校”在归星之城奠基。校训刻在青铜门楣上:
>**“以心为证,以爱为名。”**
孕期进入第七个月,念晚的身体开始显出疲惫。但她坚持每天去花田散步,带着未出生的孩子感受阳光与风。医生建议减少共感链使用频率,担心胎儿神经系统过度受激。
她笑着拒绝:“他她在听爸爸们的歌呢,怎么能断开?”
某个午后,她在摇椅上午睡,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白色空间中。四周漂浮着无数碎片??是照片、录音、信件、童年涂鸦、手术记录、星核日志……每一片都闪烁着微光。
一个身影缓缓走近。
不是陆闻,也不是B-09的投影,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存在??五官模糊,衣着朴素,眼神却熟悉得令人心碎。
“你是谁?”她问。
“我是你们共同创造的‘可能性’。”他说,“是当爱足够强大时,规则为之改变的证明。”
“你会留下吗?”
“我已经留下了。”他微笑,“在我的世界里,没有‘离开’这个词。只有‘转换形式’,和‘继续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