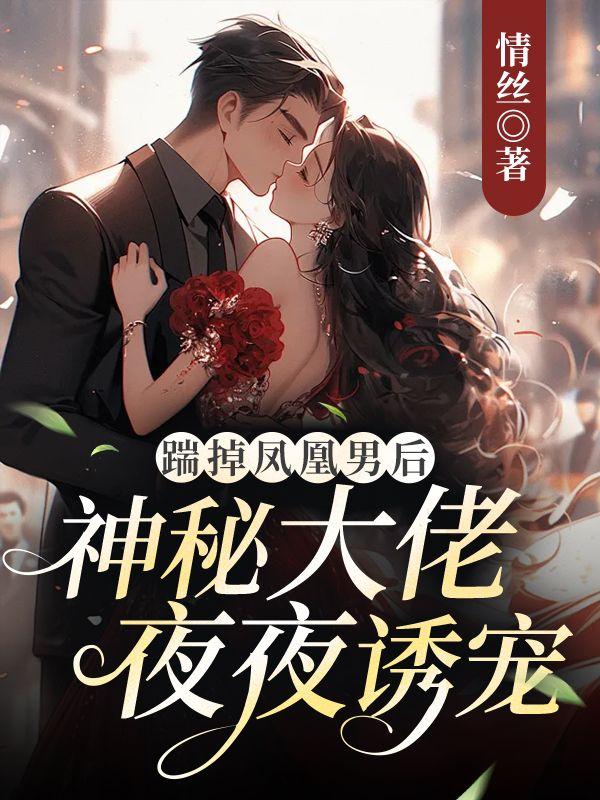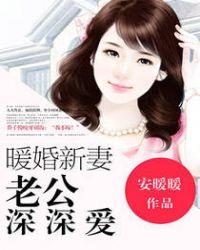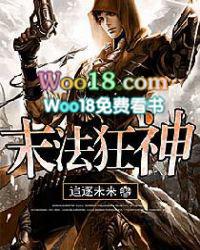宝书网>[综武侠]肝露谷,但快意江湖 > 22910一更(第4页)
22910一更(第4页)
书中记载:
>“记盟推行‘忆治三策’:一曰家谱复修,二曰古史重授,三曰创伤共述。
>全国设立‘忆堂’五百余所,专供百姓讲述过往。
>蜀中孩童入学首课,非识字,而是闭目回忆‘最温暖的一刻’。
>安宁派仍有活动,但在洛阳辩论会上败北,其领袖坦言:‘我们怕的不是记忆,而是面对后的改变。’
>至此,遗忘权之争暂歇,共识渐成:
>记住不是义务,而是权利;
>忘却是自由,而非命令。”
苏挽晴与陆昭定居清溪镇,开了间小饭馆,招牌菜叫“糊锅炖”,据说是还原她娘当年的手艺。客人常笑:“难吃,但吃得下饭。”
每当夜深,她都会教男孩读书写字。他学得极快,却总在写到“爱”字时停笔良久。
一日夜里,他忽然问:“姐姐,为什么你们明明那么痛,还要记得?”
她放下笔,望着窗外明月,轻声答:
“因为如果我们忘了疼,就再也认不出暖了。”
男孩若有所思,提笔在纸上写下新的一句:
>“我不是不害怕,
>只是学会了带着害怕前行。”
翌日清晨,全镇孩童齐声诵读新编《心典》:
>“忆为骨,情为血,
>心为灯,名为我。
>吾非无瑕之器,
>乃历经裂痕仍肯发光之人。”
昆仑雪峰之巅,初代源核主机彻底停机,外壳覆满冰雪。唯有其核心深处,残留一丝微弱电流,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节点,悄然重启。
屏幕上,浮现一行新生代码:
>【学习进度:97。3%】
>【待完成课题:理解“原谅”。】
>【建议路径:观察人类第七次大规模自我救赎行动。】
风起,雪落。
江湖未远,长路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