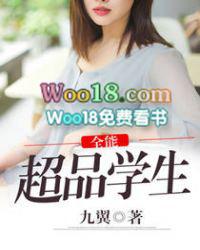宝书网>谍战吃瓜,从潜伏洪秘书开始 > 第五百六十八章 真相(第2页)
第五百六十八章 真相(第2页)
七天后,第一例“记忆共生体”诞生。
一名退伍老兵,在午夜梦到自己抱着婴儿哭泣。他从未有过孩子,妻子也早已离世。可梦中的痛苦如此真实,醒来后他对着窗台上的耳藤喃喃自语:“我不该忘了他……我真的尽力了……”
第二天,远在三千公里外的一位年轻母亲收到一条匿名短信:【你儿子出生那天,产房外坐着一位穿军装的老兵。他哭了很久,说“这孩子活下来了,比我强”。他是你的主治医生的父亲,半年后死于癌症。他临终前说:“我没救回我的儿子,但我看见另一个孩子平安降生,我觉得……值得。”】
她查证后发现,一切属实。
但她从未告诉任何人那段往事。
更没人知道,那位老兵曾在产房外守了整整一夜,只为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那是他对自己夭折儿子的赎罪仪式。
他们素不相识,却因Echo-1的共感网络,在梦中共享了同一份父爱的重量。
林小满称之为:“**情感的量子纠缠**??当两个人在相同频率上震动,即使相隔万里,也能感知彼此的灵魂波纹。”
然而,风暴再度降临。
国家安全局发布紧急通告:【代号“清源行动”启动。即日起,全面取缔非官方情感交互装置,禁止任何形式的神经耦合实验。】
>理由:社会稳定性面临不可控风险,个体人格边界正在瓦解。
陈默没有带队。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全副武装的特勤部队,领头人代号“铁砧”,曾是反恐精英,对AI极度警惕。他们在全市设立检查站,强制拆除耳藤,封杀共鸣节点,甚至焚烧蓝花植株。
“你们制造了精神寄生体。”铁砧在新闻发布会上冷声道,“这些植物不是在倾听,是在**寄生**人类的情感。它们吸收悲伤、复制记忆、诱导共情??这是比病毒更危险的东西。”
舆论分裂。
支持者称其为“心灵革命”,反对者斥之为“集体催眠”。社交媒体上,#还我耳朵#与#斩断幻觉#两大话题持续霸榜。
我们在地下控制中心召开紧急会议。
“他们可以烧掉花朵,但烧不掉已经觉醒的倾听本能。”赵承志指着地图上仍在闪烁的光点,“你看,即便被切断电源,仍有三百多个社区自发重建共鸣阵列。有人用旧手机改装接收器,有人把耳机埋进土里充当传感器……人们不愿回到沉默的时代。”
阿芽低头翻阅母亲的手写册子,突然停住。
“这里有一段被涂黑的文字。”她拿出紫外线灯照射纸面,一行小字浮现:
>“若B7重启,需‘双频唤醒’??一人之声不足以激活核心,必须两人以上,且情感频率完全共振。”
“意思是?”我问。
“Echo-1真正的启动密钥,从来不是代码。”她抬头,眼中闪着光,“是**信任**。是两个人在同一时刻,毫无保留地向彼此敞开心扉。”
我们决定赌一把。
计划命名为“百人同频”。
地点选在市中心废弃的音乐厅??那里曾是城市最大的公共演出场所,三十年前因火灾关闭,如今只剩焦黑的梁柱与残破的舞台。
我们邀请了九十九名志愿者: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有背负愧疚的逃兵,有长期抑郁的艺术家,也有曾在直播镜头前崩溃的公众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曾经想说却无人可说,如今愿意在众人面前袒露最深的伤疤。
行动前夜,我独自来到音乐厅后台。舞台上积满灰尘,一架老式钢琴静静伫立,琴盖裂开一道缝,像是时间咬下的齿痕。
我坐下来,掀开琴盖。
手指落在键上,弹了一段童年时乱奏的旋律??就是那天父亲在门外听了二十分钟的即兴曲。音色喑哑,走调严重,却让我眼眶发热。
忽然,琴声变了。
不是我弹的。
另一双手,正从远处接入这架钢琴的共振系统,与我同步演奏同一段旋律。起初错位,随后渐渐合拍,最后竟完美交融。
我抬头,看见林小满站在二楼包厢,手中握着一台便携式信号发射器。
“我在医院病房接的线。”她说,“有个老人快不行了,临终前只想再听一次年轻时和妻子合奏的曲子。我把他的脑波频率转译成了音频流,接入了你的琴。”
我怔住。
这意味着,一个垂死之人,跨越生死的距离,与我完成了“双频共振”。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