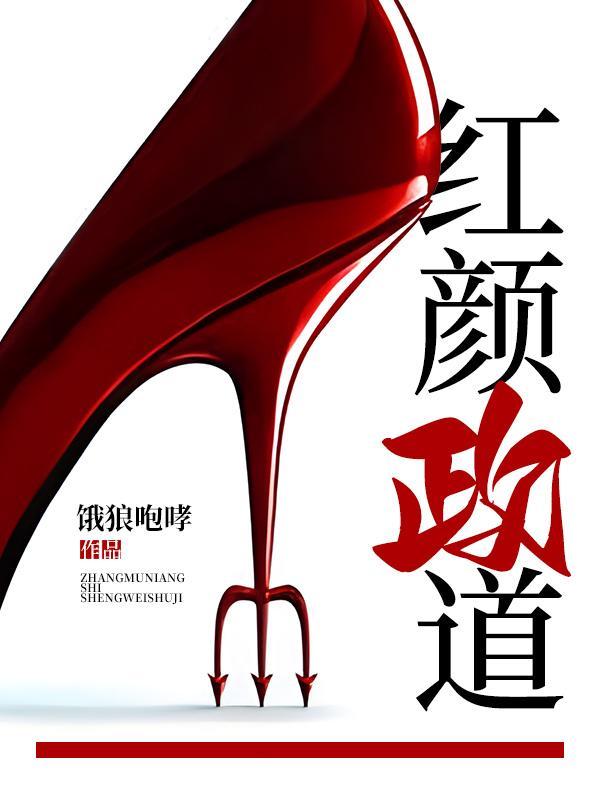宝书网>阎王下山 > 第1983章 落月村(第3页)
第1983章 落月村(第3页)
>“小星星,亮晶晶,挂在天上放光明……”
有一天,小念突然停下脚步,抬头看向夜空。
“哥,你看。”她指着北极方向,“极光又出现了。”
林既明望去,只见天际一抹幽蓝缓缓流动,如同苏醒的眼眸。
但他知道,这一次,它不再象征灾难降临,而是某种沉睡已久的秩序正在重建。
***
与此同时,远在北欧某处地下基地,一间密室警报骤响。
监控屏幕上,全球十三处灯脉节点的数据全部恢复正常波动。敦煌鸣沙山下的青铜灯桩自动复燃,昆仑墟底的星轨阵列重新校准,甚至连一度被认为永久损毁的江南水乡灯网,也开始闪烁微光。
一名白袍研究员颤抖着报告:
“报告局长……‘蚀光阵’已彻底失效。第十一号协议终止执行。编号11-0428……失踪。”
画面切换至一间空荡冷冻舱,玻璃上残留一道掌印,边缘结着薄霜。
而在控制台的日志记录末尾,赫然多出一行无法追踪来源的留言:
>**“容器已归家。从此,无人可被献祭。”**
***
两年后,南太平洋某座无名岛屿。
一所小小学校建在椰林之间,教室由旧船板拼成,黑板是刷了漆的木板,桌椅歪歪扭扭,却干干净净。孩子们大多是流浪儿、战争遗孤或实验逃犯的后代,年龄从六岁到十四岁不等。
讲台上,林既明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正教语文课。
“今天我们学一首诗。”他写下标题,《回家》。
>“我走过千山万水,
>踩碎过无数黑夜,
>只为听见一声呼唤??
>‘孩子,饭做好了。’”
学生们安静听着,有人悄悄抹泪。
后排,小念认真记笔记,手腕上的康复支架还未摘除。她现在已经能独立行走,也能正常交谈,甚至开始尝试画画。她的画册里全是厨房、餐桌、一家人围坐吃饭的场景。
窗外,阿禾牵着几个低年级孩子种花。她额头的莲花印记早已消失,但每当夕阳西下,总有一缕金光在她发梢跳跃。
铃兰坐在树荫下读信,信纸来自世界各地??
>“东京分部报告:又有三名前守夜局成员申请加入‘灯盟’。”
>“非洲营地来电:首批自建灯桩已点亮,当地孩童称其为‘希望塔’。”
>“南极科考站留言:极光频率趋于平稳,疑似与人类集体情绪正相关。”
她合上信,轻笑一声:“看来,光真的可以传染。”
黄昏降临,晚霞如焰。
林既明走出教室,看见阿禾正帮小念系围巾。三人并肩走向海边的小屋,炊烟袅袅升起,锅里的红烧肉正咕嘟冒泡,香气四溢。
海浪轻拍岸边,风铃叮当作响。
这一刻,没有使命,没有宿命,没有永夜,也没有牺牲。
只有家。
而家,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