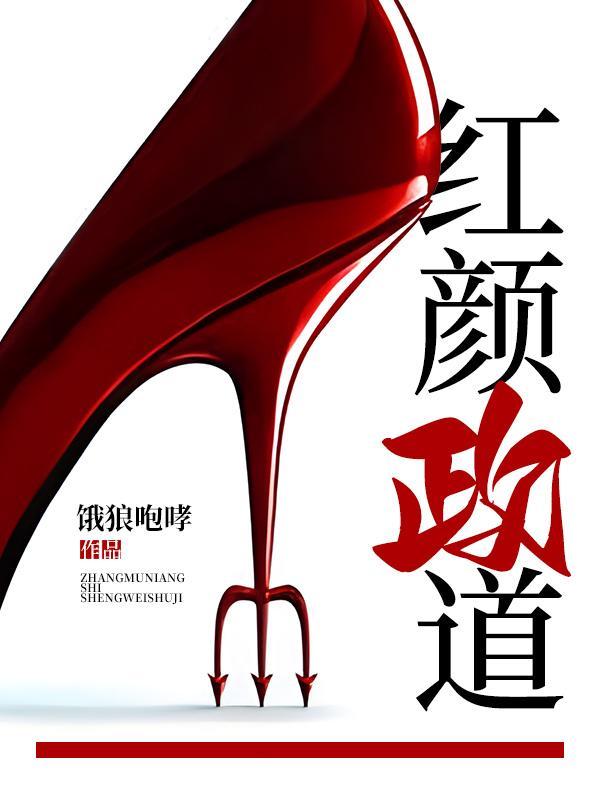宝书网>都重生了,我当然选富婆啦! > 第444章 关于家求订阅(第2页)
第444章 关于家求订阅(第2页)
“叫什么名字?”吕尧问。
“《听你说》。”她笑了笑,手指轻轻拨弦,“写给所有没被人听见的人。”
>“你说的话飘在风里没人抬头看天际
>你说的痛藏在笑容里连眼泪都静音
>可我知道你在呼吸在黑暗中轻轻叹息
>所以我来了带着耳朵也带着心……”
歌声未落,门铃又响。
门外站着一位陌生老太太,拄着拐杖,手里紧紧攥着一台老旧MP3。
“你是吕尧先生吗?”她声音沙哑,“我是李秀兰的女儿。我妈去年走了……走之前留下这个,说一定要交给‘火种’的人。”
吕尧接过MP3,小心插入读卡器。里面只有一段录音,背景杂音很重,像是在医院病房。
>“各位好,我叫李秀兰,七十九岁,肺癌晚期。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两个月。我不怕死,但我怕没人知道我心里的话。”
>
>“我年轻时是纺织厂女工,结婚早,丈夫脾气暴,打得我好几次住院。我不敢说,怕丢脸,怕孩子受牵连。后来女儿长大了,嫁了个家暴的男人,我劝她忍,说‘女人就得认命’。结果她真的忍了二十年,直到被打断肋骨才离婚。”
>
>“我现在后悔啊……要是当年有人听我说一句‘我很疼’,也许我就不会把同样的苦咽下去,也不会让她也吃这一遭。”
>
>“所以我想借你们这个平台说一次:我不是坚强,我是不敢哭。我不是伟大母亲,我是被困住的女人。”
>
>“如果有谁正在经历这些,请别学我。说出来,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见,也好过自己扛一辈子。”
录音结束,满室静默。
陈素芬早已泪流满面。“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她们不是不说。”吕尧轻声道,“是我们一直没准备好去听。”
当晚,他又一次打开直播,没有预告,没有标题,镜头对准空荡的客厅中央,只放着一把椅子。
他坐在对面,平静地说:“今晚,我想做一个倾听者。如果你愿意,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匿名也好,露脸也好,我都听着。时间不限,人数不限。只要你需要,这个房间就为你亮着灯。”
消息一经发布,请求接入的申请如潮水般涌来。
第一位是一位高中生,颤抖着说出自己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整整三年没人相信他;第二位是位独居老人,儿子在国外十年未归,她每天对着冰箱说话,因为“它会回应冷气”;第三位是一名transgender青年,哽咽着讲述父母把他关进精神病院强制“矫正”的三个月……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谢谢你还开着灯”。
整场直播持续了十三小时,共收到217条有效倾诉。其中68条触发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平台立即联动当地社工组织进行干预。
第二天,《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报道,称其为“一场温柔的革命”。央视新闻评论:“真正的文明,不在于高楼有多高,而在于是否容得下一个普通人说出‘我不快乐’。”
而吕尧知道,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十八岁那年,他在雨夜里听见母亲最后一声叹息。
几个月后,“寻声之旅”迎来里程碑时刻:第50万次响应达成。系统数据库已收录超过十万段真实录音,涵盖137种语言及方言,包括濒危民族语、手语变体、甚至婴儿啼哭的情绪分析模型。
更令人惊喜的是,阿米娜团队成功将“心灵图谱”技术应用于自闭症儿童早期干预。在北京一所特殊学校试点项目中,一名五岁男孩首次通过脑波可视化表达了“我想妈妈”,让分离八个月的母亲当场崩溃大哭。
与此同时,陈素芬正式重启个人音乐计划。她的首张专辑命名为《静音区》,全部歌词来源于“火种”平台上匿名用户的倾诉片段。主打歌《有人在听》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并被选为联合国妇女署公益宣传片主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