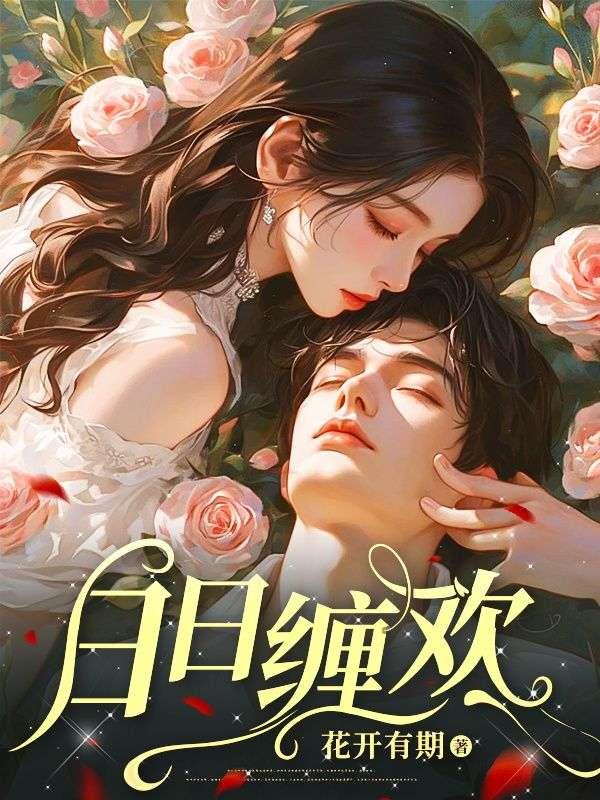宝书网>盘臣 > 4050(第28页)
4050(第28页)
五指微微收拢。
他厚实的背肌肉眼可见一阵痉挛。
言子邑难得听见他的呼吸声:
“我出京在即,此行意在宣慰军士,不能蜻蜓点水,得留一阵,我怕你怀了我的孩子,一人在府不方便。”
言子邑笑了,不禁拍了一下他的背。
他背肌紧实,轻轻一拍也“啪”地一声。
——王爷这自信……哪来这命中率这么高。
一下子又隐隐感受到他此行可能有危险。
“王爷,”她抬起双臂将他搂近一些,
“我嫁过来之前,四弟问过我,想嫁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想嫁个正常人。王爷在我看来,一直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人。可……别让我失望……”
床围子内忽然一静。
他扶在腰间的手慢衍而上,目光和拇指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不动,像平时那样捻了两下。
言子邑的笑僵在脸上,感受到那一点的胀凸,言三小姐偏瘦的身体,竟然这样敏感。
“来。”
靳则聿的捻动和思考一样,是很快作了决定的。
捉住她的一只小臂,将它从后背拉了回来,把着她的手,引着她一下子就握到了一个勃跳的所在。
“愣什么?”
相比他而言,自己纯然是一种虚张声势,随生随灭。
言子邑耳后发胀。
好像刚刚给自己灌注的野性,一下子就凝冻了。
自己的手,被他主宰着循序往复,就像不长在自己身上。
言子邑觉得自己从虎口到手腕。
像鼓了一道热流,手心里嵌的东西,要嵌到心脏里一样。
他的表面还是一样的静。
但看着她的眼神是一种专横,不容你拒绝的。
像静淌着的河流里的暗流,骚动是压在很底端的地方。
……
因按陛下的旨意,靳则聿是奉旨至军中宣慰军士,故十月廿一,城中百官于一早便于城门口候立,迎送靳王出城,因是宣慰军士,只带了三千兵马,京城北门原辰初通行走,今日寅时便有人扫雪,寅正便已有人在此把守,天此时还零星飘了些雪花,且李通涯增了两倍人手,在崇安门街上疏散将要过北门的百姓,奉王命,请宫中太监着看仪仗如何行走,从驾于何处归仪等等。百官是提前一个时辰在城门口送行,因未曾想有雪,也未搭置芦竹棚帐之类,一个个呼着白气,也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原地呵一下手掌。
按规制,女眷不能迎送,言子邑坐在马车里,远远的望着,不着痕迹。
陛下的卤簿仪仗从宫门口驰来,就听见前头一喊:
“百官跪接!”
接着炮鸣声从城门楼上乍起,丝竹钟罄盖着文臣武将的山呼万岁,一下子打破了寒天的冷寂。言子邑不由看着冻了一个时辰的言家二哥,刚随班起身,便捂着手斜看城楼礼炮,似乎在默数礼炮声,像是担心出了哑炮。邢昭甲胄在身,是随在陛下身旁,中规中矩,老秦从这么远望去,也能觉得心怀不定……言子邑从人群中寻了一遍认识的面孔,发现也没有几个,最后还是落到了王爷身上。
陛下从车驾上下来,踩了踩已扫过雪的地,于众人间扫了一眼,便笑着虚扶一把在身前行礼的靳则聿。
望着他行止有度的身影。
耳畔依旧是黄钟大吕的震颤,伴着丝竹礼炮,灌得仿佛经久不绝。
一下子觉得有些伤感。
或是马车停在的这个静僻的角落,显得自己与前头的事无关。
觉得自己很多该做的事情没做。
很多该问的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