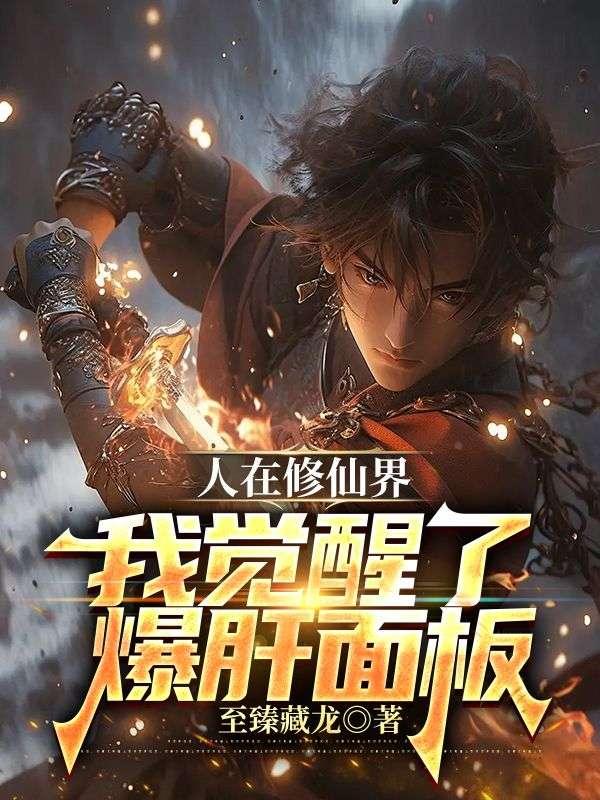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战锤:我的生物爹帝皇和半神弟弟 > 第553章 钟鸣鼎食我们把王妃烹了吧3K(第1页)
第553章 钟鸣鼎食我们把王妃烹了吧3K(第1页)
“真是想不通,奸奇那鸟玩意怎么想起来生孩子的,还是和纳垢?”
“怎么着也应该去找色孽啊。”
公园前599年,国王寝宫。
正在从黑王的所得之中获取记忆的安达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
亚伦的指尖仍贴在棺椁表面,涟漪般的波纹尚未散去。他的掌心传来一阵奇异的搏动,仿佛金属之下藏着一颗心脏,正与他体内的某种节律悄然同步。那不是血肉的心跳,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宇宙呼吸般的频率??每一次震颤都牵动着他脊椎深处沉睡的神经束,像是有无数细小的触须从骨髓中探出,沿着血管攀爬,直抵大脑皮层。
“你感觉到了吗?”夏光佳低声问,手中握着一块刻满死灵符文的水晶片,其内部光芒如潮水般涨落。“共鸣场正在扩展……不只是这间密室,整个地下结构都在共振。”
亚伦没有回答。他的视野已经开始模糊,眼前的墙壁不再是石材砌成,而是浮现出层层叠叠的记忆残影:一片灰白色的平原上,七座倒悬的塔楼如同根须刺入天空;一条由碎骨铺就的道路延伸至horizon,尽头是一座无门的宫殿;而在那门前,站着七个背影??和他们一模一样,却又截然不同。那些身影身上缠绕着锁链,锁链的另一端深入地底,连接着某种巨大到无法形容的存在。
“他们在等我们。”亚伦喃喃道,“不是召唤,是……接引。”
小荷鲁斯冷笑一声,一脚踹翻了旁边堆放的工具箱:“接引个鬼!老子可不想被谁当成祭品塞进什么神明肚子里!”但他眼神却亮得惊人,像燃烧的铁水,“如果真有‘第二帝皇’,那就让我亲手把他拽出来审问!凭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凭什么让我们兄弟相残、千年不得安宁?”
列奥尼多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如纸。他原本想离开,去向父亲报告这一切异常,可脚步却像被钉住一般动弹不得。他听见自己内心有个声音在低语:“你怕的不是真相,是你发现自己一直效忠的是个谎言。”他猛地咬破舌尖,血腥味让他清醒了一瞬,但随即又陷入更深的混乱??他竟分不清这念头是来自自己,还是来自那个曾在梦中呼唤他名字的幽影。
马鲁姆蹲在地上,用匕首在地面划出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将棺椁置于中心点。他一边绘制一边低声念诵,那是禁忌的知识,源自他在远征途中从一座被遗忘的机械神庙中盗取的卷轴。据说,这种符文能短暂撕裂现实的表皮,让观察者窥见“原初之网”??即所有可能性交织而成的命运织锦。
“看。”他忽然抬头,声音沙哑。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空气中浮现出一道半透明的影像:七颗星辰排列成环形,每一颗都对应一名原体的位置。其中六颗稳定发光,唯独第七颗??代表亚伦的那一颗??正剧烈闪烁,仿佛随时会熄灭,又似即将爆发。
“这不是预兆。”夏光佳眯起眼,“这是实时映射。我们在改变它。”
“所以仪式已经开始?”列奥尼多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哪怕我们还没动手?”
“不。”亚伦缓缓站起身,抹去鼻腔再次渗出的黑血,“仪式早就开始了。从父亲把我们召回泰拉那一刻起,从他让我们参与‘空中花园’建设那一刻起,甚至……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他望向壁画上的七人连环,“我们不是参与者,我们是祭品本身。但现在??我们要成为主祭。”
钟声再度响起,比先前更加沉重,像是敲击在灵魂之上。工地上的人群开始撤离,脚步匆忙而有序。宵禁已至,整座城市进入静默状态。唯有那尚未完工的空中花园仍在微光中矗立,宛如一只半睁的眼睛,凝视着夜空。
一夜无眠。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安格隆来了。
他没有乘坐任何载具,也没有护卫随行。他就那样赤着上身,披着染血的斗篷,一步步踏过石阶走入密室。每走一步,地面都会因高温龟裂,空气中弥漫着铁锈与焦肉的气息。他的双斧挂在背后,刀刃上还滴着未干的血??不知是敌人的,还是他自己的。
“你们吵了一整晚。”他声音低沉,带着角斗士特有的沙哑,“我都听见了。”
小荷鲁斯咧嘴一笑:“怎么,终于肯走出你的竞技场了?我还以为你要等到世界末日才肯清醒一次。”
安格隆没理他,径直走向棺椁。他在距离三步远的地方停下,盯着那道裂缝看了许久,然后突然笑了:“原来如此……难怪我每次杀人的时候,脑子里总会闪过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那些尖叫,那些哀求……都不是战俘的,是?的。”
“你也梦见了?”亚伦问。
“不止梦见。”安格隆抬起手,掌心朝上。一道金色的符文缓缓浮现,形状与亚伦之前流出的血液蒸发后留下的痕迹完全一致。“?在我体内埋了种子。每一个原体都有。只是有些人选择遗忘,有些人假装听不见。”
“那你现在听见了?”马鲁姆问。
“我一直听得见。”安格隆冷笑,“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怕一旦承认,就会忍不住冲上去砸开这棺材,跪下来亲吻?的脚踝。”
空气骤然紧绷。
“所以你是知道的。”亚伦轻声道,“你知道‘第二帝皇’是谁,也知道?为何被封印。”
安格隆沉默片刻,终于点头:“我知道。因为……我也曾是?的一部分。”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不可能!”列奥尼多怒吼,“你是吞世者,是战帅之子!你怎么可能是??”
“我是谁的儿子?”安格隆猛然转身,双眼泛起猩红,“你以为荷鲁斯真的只创造了我一个实验体?不。他是第一个尝试‘完美战士’的造物主,而我……是最接近失败的那个。我的大脑无法承受完整神性,所以他们把我拆开,把属于‘?’的那一半意识封存在王座之下,另一半则扔进角斗场,任其在痛苦中重生千百次。”
他指着棺椁:“每当我在战斗中濒临死亡,那一半就会苏醒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能一次次复活,为什么我的愤怒永不枯竭??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两个意志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