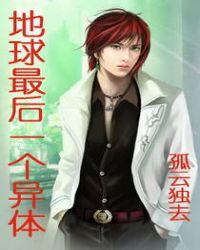宝书网>三国:昭烈谋主,三兴炎汉 > 第476章 刘李之争已入高潮加更(第2页)
第476章 刘李之争已入高潮加更(第2页)
>“真实之外,尚有仁心。”
他抚摸那字迹,指尖发烫。
归途上,他不再沉默。每经一城一镇,便寻共语堂登记口述稿,讲述云溪村的故事,讲述曾祖父的挣扎,也讲述老妪的眼泪。他写道:“正义不是非黑即白的判决,而是理解所有灰色地带后的选择。”
这篇《云溪七姓书》迅速传开,被收入地方共述档案,并引发新一轮讨论:是否应对历史执行者设立“悔赎通道”?即允许后代以其善行抵消先人部分名誉污损?朝廷尚未定论,但民间已有三十六个家族主动提交类似申请。
与此同时,京都共语堂召开特别议席,审议一项提案??将“共述教育”正式纳入太学必修课程,内容涵盖记忆伦理、创伤叙述、跨代责任等九门科目。主推者正是沈明澜之徒,年仅二十的林照。
议席之上,一位老儒生怒斥:“此乃动摇纲常!祖宗之罪岂容子孙辩解?”
林照起身,平静道:“正因为是祖宗之罪,才更需子孙面对。否则,仇恨将在血脉中代代相传,直至爆发。”
他又出示一份数据:近五年因家族记忆冲突引发的命案下降六成,而跨族群和解案例增长四倍。“共述不是揭伤疤,而是教人包扎伤口。”
最终提案通过。同年秋,首批共述学堂在边陲十郡开课,教材由阿织亲审,首章标题为《倾听比说话更难》。
这一年冬天,阿织接到消息:陈延已抵玉门关。
她立即启程北上。两人相见于敦煌鸣沙山下,夕阳如血,驼铃悠远。陈延苍老许多,鬓发尽白,可眼中光芒不减当年。
“老师。”他跪地叩首。
阿织扶起他,颤声问:“龟兹的歌谣,真的能承载真实?”
陈延微笑,取出一枚异形忆玉??形如竖琴,触之即响。他轻轻一拨,空中浮现光影:一名老牧民坐在帐前,唱着古老史诗,旋律流转间,文字自动浮现,记录下一段被遗忘的和谈往事。
“他们用歌声传递历史,我教他们用忆玉保存歌声。”他说,“十三座吟语塔,每夜都有百姓登台放歌。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忏悔,有人感恩。西域诸国已开始互派共述使节,交换口述史。”
阿织含泪而笑:“你把共述种成了树,还在开花。”
不久后,朝廷设“西史馆”,专录西域共述成果。皇帝特旨召陈延入京,欲授礼部侍郎。他婉拒:“我愿做一辈子的记录者,不做官。”只请求在京都建一座“音心阁”,仿吟语塔制,供百姓以歌证心。
三年后,音心阁落成。首个登台者竟是当年纵火少年,如今已是明烬书院讲师。他弹琴而歌,歌词源自祖父部落的哀诗,译为汉文:
>“马蹄踏碎家园时,母亲抱着婴儿跳崖;
>百年后孙子抄书时,汉人孩童递来清水一碗。
>仇在哪一天结束?爱又从何处开始?”
歌声落下,全场寂静,继而掌声如雷。
又五年,南海再起风波。一伙自称“忘川余烬”的秘密结社暗中活动,散布谣言,煽动民众焚烧忆玉,宣称“唯有彻底遗忘,方可重生”。其首领竟是一名曾参与共述改革的前官员,因家族丑闻曝光而失势,心生怨恨。
朝廷震怒,下令彻查。沈明澜却建议:“不必剿灭,召之共语。”
于是,在岭南共语庭设“忘川听证”,邀请该首领登台陈述。
那人昂首而入,厉声道:“你们打着真实的旗号,实则施行精神暴政!逼人自曝隐私,逼子揭父,逼妻告夫!这不是共述,是酷刑!”
台下哗然。
沈明澜起身回应:“你说得对??若共述沦为强迫,便是新的tyranny(暴政)。但我们从未要求任何人必须上传记忆。《共述律典》第一条写得清楚:知情同意,自愿为先。”
他转身调出数据库,“过去十年,全国共接收个人记忆条目三千二百万余条,其中主动撤回者逾百万。无人因拒绝共述受罚。真正的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心恐惧。”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你恨的,或许不是共述,而是那个不得不面对自己不堪过去的自己。”
那人浑身剧震,久久不语。
三日后,他主动交出组织名单,并在共语庭公开忏悔:“我烧毁的不是谎言,是我自己的羞耻。可羞耻不该由别人承担。”
事件平息后,朝廷颁布新规:严禁任何形式的记忆强制采集;设立“沉默权日”,每年清明前三日,全国忆玉系统关闭,象征尊重个体遗忘的权利。
人们这才真正懂得,共述的终极意义,不在逼迫所有人开口,而在确保每个人??无论想说或不想说??都能被平等对待。
时光荏苒,又是一纪轮回。
阿织九十岁那年,病卧东海小屋。窗外海浪拍岸,一如她初登岛时的夜晚。陈延、沈明澜、林照齐聚床前。
她握着他们的手,气息微弱:“我这一生,最怕的不是敌人强大,而是我们变得像他们一样??用真相去压迫他人。”
众人垂泪。
她最后说道:“记住……共述不是为了审判过去,是为了让未来还能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