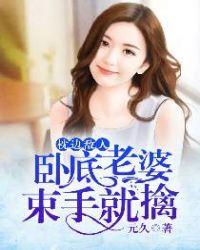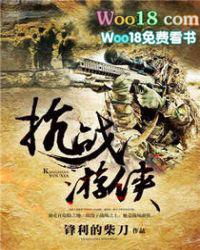宝书网>三国:昭烈谋主,三兴炎汉 > 第463章 时过境迁不变的只有关羽的刚直正义(第3页)
第463章 时过境迁不变的只有关羽的刚直正义(第3页)
“我记得。”
接着是第二个:“我也记得。”
第三个、第四个……直至百人齐诵:
>“我记得。”
>
>“我们记得。”
>
>“汉未亡,只是睡着了。”
>
>“我们会叫醒它。”
话音落下,井水翻腾,一道螺旋状蓝光直冲云霄,贯穿乌云,竟在高空形成一圈环形极光,宛如天眼睁开。
千里之外,孟魇最后的化身??那位始终隐身朝堂的“影诏”??正在批阅奏章。忽然,他手中的朱笔断裂,墨汁溅上纸面,竟组成四个字:
>“你已被忆。”
他猛地起身,望向南方,脸色惨白如纸。
他知道,完了。
不是死于刀剑,不是败于权谋,而是被千万人的记忆活生生拖回历史审判庭。他曾以为可以抹去一切,重塑万民心智,却忘了人类最原始的力量:**讲述**。
从此以后,无论他躲在哪里,都会有人在夜里说起他的罪行,孩子会在游戏中扮演他的覆灭,诗人会把他的名字写进讽刺长诗。他将成为传说的一部分,永远钉在真实的耻辱柱上。
黎明彻底降临。
山巅旗帜仍在飘扬,尽管布面已薄如蝉翼,经不起一次强风。但没有人去换新的。因为它早已不是一面旗,而是一种象征:即使褪色、破损、孤立无援,只要还在风中舞动,就说明还有人不愿遗忘。
多年后,史家记述这段岁月,称之为“贞音之世”??
一个没有官方定论的时代,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史官的时代。
书籍不再由朝廷垄断编纂,而是由村落、家族、行会自发传承;
学校不再教授统一课本,而是鼓励学生走访长者,收集口述往事;
甚至连祭祀仪式也发生变化:人们不再只祭拜帝王将相,也开始为“无名记述者”设立牌位,香火不断。
至于那口古井,始终未曾干涸。每逢夏至,总有孩童前来敲击,等待那一声“叮”响起。有人说,只要这声音不停,火焰就不会熄灭。
而火焰之后,终将迎来新的春天。
某日清晨,一位旅人路过南中,见一群孩子围坐井边,轮流讲述各自听来的旧事。一个小女孩说得兴起,脱口而出:
“我爷爷说,刘备其实没死在白帝城。他是诈亡脱身,化名游历天下,只为寻找失落的《炎汉真谱》。他还见过一个背着铜匣的瞎和尚,两人在峨眉山顶说了三天三夜的话……”
众人哄笑,说她胡编。唯有那少女静静听着,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她没有打断,也没有纠正。
因为她知道,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有人愿意相信,并继续讲下去**。
语言不死,记忆不亡。
而每一个敢于开口的人??
都是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