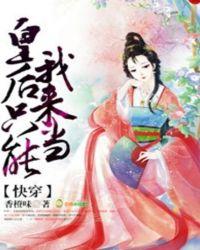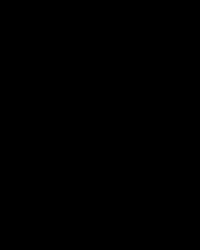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66章 此人品行不端万不可成为王夫(第1页)
第1966章 此人品行不端万不可成为王夫(第1页)
暴雨过后,山谷的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草尖上挂着露珠,每一颗都像一面微缩的镜,映着灰白的天光。那块无字石碑静立中央,仿佛自古便在此处,又仿佛昨日才从地底浮出。风过时,草叶摩挲之声不绝,如同千万人低语,却无一句成形。
小女孩蹲在碑前,指尖轻轻划过泥土。她已不是当年那个穿补丁衣裳的孩子了,鬓角染霜,背也微微佝偻,但眼神依旧清澈,像未被浊世浸染的井水。她望着自己方才写下的两字??“你说”??随即用手掌抹去。动作轻柔,如同抚平一个孩子的梦。
她知道,这土地不需要碑文。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由无数开口说话的人一笔一画刻下。那些话不在纸上,不在诏令里,而在母亲哄睡孩子时的一声叹息,在农夫犁田时对老牛说的那句“你也累了”,在书生撕毁功名帖时喃喃的“我不想再骗自己”。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是成人的稳重步伐,而是孩童奔跑时特有的杂乱节奏,夹杂着笑闹与喘息。七个孩子冲进草地,手里攥着纸笔,脸上溅着泥点。领头的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约莫六七岁,跑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停在石碑前。
“婆婆!”她喊,“我们来啦!”
老学者抬起头,笑了。“怎么,今天轮到你们说话了?”
“嗯!”小女孩用力点头,“老师说了,每个人都要来找这块石头,说一句心里最怕说出来的话。”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孩子们互相看看,有人咬唇,有人低头踢土。终于,一个瘦弱男孩举起手:“我先来。”他走到碑前,深吸一口气,声音发颤:“我……我不喜欢爸爸的新妻子。她说我乖,可我觉得她在看我的笑话。我娘走的时候,她还在笑。”
话音落,他整个人松了下来,眼眶却红了。其他孩子静静地看着他,没人嘲笑,也没人打断。
接着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我考试抄了同桌的答案。不是因为我不会,是因为……我怕考不好,妈妈又说我没用。”
又一个男孩低声说:“我偷看了哥哥写给妹妹的信。上面写着‘我想死’。我没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怕他也恨我。”
一句接一句,如雨滴落入干涸的河床。这些话本该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在这里,它们落地后竟化作轻烟,随风散开,反而让人心头一松。
老学者听着,眼角湿润。她想起三十年前,自己也是这样站在树下,第一次说出“我不愿意嫁给县令的儿子”。那时她以为会遭雷劈,结果只是风吹过耳畔,像谁在轻轻应和。
如今言树虽不见,但它早已不在某一处。它活在每一次颤抖的嘴唇间,活在每一个终于敢直视对方眼睛的瞬间。
就在这时,一名少年从山坡另一侧缓缓走来。他身形高大,面容冷峻,手中提着一只破旧木箱。孩子们见了他,纷纷退后几步??这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游学的学子。他的衣袍是深青色的,袖口绣着极细的银线纹路,像是某种官府标记,却又被刻意磨去了痕迹。
老学者站起身,目光沉静。“你是谁?”
少年停下脚步,低头看着箱子,良久才开口:“我叫归尘。来自北境‘静雨实验’的最后一座观测站。”
空气骤然凝滞。
这个名字,曾是噩梦的代号。当年共议阁以“安定民心”为名,在极北之地秘密筛选孤儿,测试“归心露”的初期版本。服用者不会反抗,不会质疑,甚至会对施害者微笑致谢。而“归尘”,正是那批孩子中唯一存活至今的名字??因为他从未真正服药,而是被选为观察记录员,被迫写下同伴如何一点点忘记痛苦、爱上谎言的过程。
“你来做什么?”老学者问。
“还债。”他说,打开木箱。里面是一叠泛黄的手稿,封面用血写着三个字:**真名录**。
“这里面记着三百二十七个人的真实姓名、出生地、亲人名字。他们被编号代替,被药物洗脑,最后死在冰原深处。他们的记忆消失了,但我的笔记得住了。这些年,我走遍十六州,找到还能联系上的家属,把名字还给他们。”
他顿了顿,声音沙哑:“可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想认回这个名字了。他们说:‘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愿效忠朝廷的‘安语义士’,也不愿承认曾被人操控一生。”
老学者沉默片刻,忽然问道:“那你呢?你还记得你自己吗?”
归尘怔住。
“你说你叫归尘,可那是他们给你起的名字。你本来叫什么?”
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
“你看,”她轻声道,“最深的毒,不是让人说谎,而是让人忘了自己曾经想说什么。”
归尘缓缓跪下,将箱子放在石碑前。然后,他从怀中取出一支炭笔,翻开手稿最后一页,开始写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清晰可闻,像是刀刃刮骨。
写完后,他把那页纸撕下,递给老学者。
纸上只有一行字: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但我知道我不想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