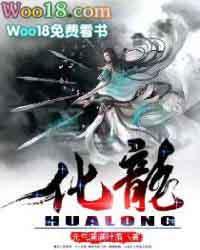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65章 他活着天下君王都得低眉(第2页)
第1965章 他活着天下君王都得低眉(第2页)
剑未落下,一道灰影闪过,阿枝拄着拐杖挡在树前。他已老迈,白发如雪,左腿是木制假肢??十年前为护言树,断于共议阁余党的火攻之下。但他目光依旧锐利,如同当年那个在井底抄录遗言的少年。
“砍吧。”他说,“但你要想清楚,这一刀下去,不只是伤树,更是斩断你自己心里刚刚冒出来的一点真。”
持剑者手臂僵住。
阿枝转向那首领:“你们还在用‘秩序’当盾牌,可你们忘了,真正的混乱从来不是来自多说话的人,而是来自不敢说话的人终于爆发的那一刻。你们压制三十年,换来的是千万个夜晚的噩梦、夫妻间的沉默、父子之间的猜忌。现在,这里的孩子至少还能哭出声来。”
使者久久不语。最终,他缓缓收剑入鞘,摘下腰间铜铃,放在地上。
“我申请……留下听一课。”他说。
其余人陆续解铃,堆成一座小小铃冢。
夕阳西下,老妪继续教字。新来的学生里多了几个曾执掌笔政的老儒、两名退役的禁军密探,还有一个从南疆逃回来的忘忧蜜试药人??他花了整整一年才重新记起自己的名字。
夜深,篝火燃起。有人问:“真的不会再有共议阁了吗?”
阿枝望着星空,轻叹:“毒蛇死了,蛇窝塌了,可土里的卵还没灭绝。只要还有人觉得‘安宁’比‘真实’重要,就会有人想重建高台,再造幻象。”
“那怎么办?”
“守着树。”他说,“种语不停,真话就不会断根。哪怕只剩一人记得怎么开口说‘不’,火种就在。”
忽而,一阵清风掠过,卷起几张旧纸条。那是豆芽化作风前留下的残页,上面字迹早已模糊,唯有反复摩挲之处,透出淡淡光晕。纸片飞旋上升,绕树三圈,竟在空中拼出一行短暂存在的文字:
>**不怕说错,只怕不说。**
孩子们拍手欢呼,以为是奇迹。只有阿枝知道,这不是神迹,而是共振??当千万人同时想起同一个名字,记忆本身就成了力量。
第二日清晨,使者们离去,未带一人一物。但他们带走了一样东西:每个袖中都藏着一张沙地拓印,写着一句孩子亲口说出的“实话”。
数日后,京城传出消息:安语司遗址上,有人搭起一座草棚,挂匾曰“今日我说实话”。第一天,仅一人前往。第五天,排队长达百米。第十天,一名尚书微服前来,跪在棚中三时辰,出来时满脸泪痕,回府即上辞表。
与此同时,南疆边境,忘忧蜜作坊接连起火。调查发现,纵火者竟是曾服用此蜜的富商本人。他们在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毁所有库存,并在墙上写下:
>“我记得她死时睁着眼,而我当时笑着说‘挺好’。”
>“我不该忘记。”
风暴不再由一人掀起,而是自千家万户的灶台、床头、学堂角落悄然汇聚。有人说,这是豆芽的魂魄仍在游走;也有人说,是小满的骨笛余音未散;更有人坚信,言树开花那天,天地之间便多了一种律令??**凡心有所念,终将出口**。
然而,真正的考验尚未到来。
某夜,暴雨倾盆。一名浑身湿透的少女踉跄闯入山谷,怀里紧抱一只陶罐。她双目通红,嘴唇开裂,见到阿枝便跪地痛哭:“我是北境‘静雨实验’的幸存者……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药剂……叫‘归心露’……”
她断续讲述:共议阁残部并未消亡,而是转入极北冰原,在废墟深处重建实验室。他们吸取过往教训,不再强行压制言语,也不再制造幻象,而是研发一种能让人“自发认同谎言”的药剂。服用者会真心相信官方叙事,甚至主动劝导他人:“何必纠结真假?我们现在很好。”
“最可怕的是……”少女哽咽,“它通过饮水传播。一座城只要有一人使用,七日内全城皆染。他们会笑着删改史书,唱着歌焚烧日记,把真相当成疯病治疗。”
阿枝脸色铁青。他知道,这一次,敌人不再站在对立面,而是**钻进了每个人的脑子里,成了他们自己**。
他立即命人封闭山谷水源,加固言树周围结界。但更紧迫的是:如何唤醒那些已经“自愿沉睡”的人?
三天后,老妪做出决定。
她召集所有孩童,每人发一张白纸、一支炭笔。“你们要去做一件很难的事。”她说,“去见你们住在城里的亲戚,把这张纸给他们看,然后问:‘你还记得吗?’”
纸上什么也没画,只有一个日期??那是他们父母或祖辈说出第一句真话的日子。比如:“三月初七,爹在粮仓外说了实话。”“腊月十九,娘哭着承认哥哥是被官府抓走的。”
孩子们懵懂出发,带着空白的纸,走向那些已被“归心露”浸染的城市。
起初无人理会。人们看到纸,只温和一笑:“小朋友,这是作业吗?做得真认真。”或者:“啊,今天天气不错,适合出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