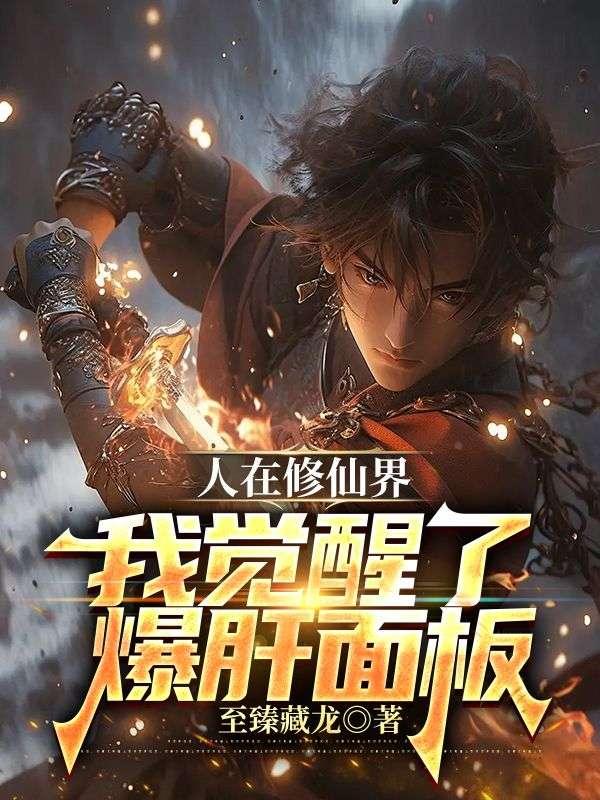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63章 只打高端局(第1页)
第1963章 只打高端局(第1页)
武王吓了一跳,连连摆手,“可千万别,嘴下留情。”
宁宸笑了笑,旋即吩咐一个士兵,“你进去看看,她家有多少副碗筷?上面是否有落灰?”
“是!”
士兵领命而去。
武王不解,“你查这个做什么?”
“一会儿再告诉你,目前还不确定。”
没一会儿,前去查看的士兵回来禀报,“启禀摄政王,这家一共二十一只碗,二十七双筷子,洗得很干净,没有落灰。”
宁宸挥挥手,示意士兵退下,然后冷笑一声,目光落到那女子身上,“年纪不大,。。。。。。
夜色如墨,初音井畔的风却带着温润的气息,像是大地在缓缓吐纳。豆芽坐在井沿上,指尖轻轻划过水面,涟漪一圈圈扩散,映着星河摇曳。她已在此静坐三日,不食不眠,唯有呼吸与地脉同频。阿枝守在一旁,手中握着一支断裂的骨笛??那是昨夜从北境飞来的信使所携,笛身裂痕中渗出暗红血渍,仿佛诉说着千里之外的悲鸣。
“十七座驿站,已有九处失联。”阿枝低声说,声音像被风吹散的灰烬,“沈知白最后传来的讯号是在洛阳城外,他说……‘他们开始收编真语’。”
豆芽闭目,眉心微蹙。她听到了。不只是阿枝的话,更是那遥远土地上传来的撕裂声??有人正试图将“无名大会”上的真言重新编码、归档、美化,甚至供奉为新的经典。共议阁并未放弃,反而换了一种更狡猾的方式:他们不再禁止说话,而是将真实的话语制成标本,陈列于庙堂之上,称之为“圣训”,实则抽去其血肉,使其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太平辞典》。
“他们在驯化真相。”豆芽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就像把野马套上金鞍,让人误以为自由仍在奔跑。”
话音未落,地面忽有震颤。一道微弱的光自东南方蜿蜒而来,如萤火游走于地底。阿枝猛然抬头:“是墨脉回流!”只见那光芒渐强,竟携带着无数细碎语声,似哭似笑,似咒似歌,汇入初音井底。井水骤然翻涌,浮现出一行行流动的文字,如同活物般交织成图:
>“我娘死前攥着我的手说:别替他们写颂词。”
>“我们村三年没下雨,官府却报‘风调雨顺’。”
>“我知道皇帝根本没退位,只是换了名字活着。”
这些话语并非出自一人之口,而是千万人压抑多年后,在梦中、在醉里、在临终前喃喃吐露的片段,如今竟顺着净化后的墨脉自动汇聚至此。它们不成章法,却真实得令人窒息。
豆芽伸手触碰水面,指尖传来刺痛,仿佛每一个字都在咬她。“这不是记录,”她喃喃,“这是记忆的反噬。”
就在此时,山谷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人,而是成群结队,踏雪而行。阿枝警觉起身,却被豆芽抬手制止。来者并非敌军,而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有老者拄拐,孩童背负行囊,妇人怀抱婴儿,男子肩扛残破陶铃。他们脸上写着疲惫,眼中却燃着光。
为首的老儒生跪倒在地,额头触雪:“草民……来自兖州。我们走了四十九天,只为亲耳听见一句真话。”
豆芽扶起他,问:“你们如何知道此处?”
老人颤抖着从怀中取出一片海贝:“昨夜梦中,它自己开了口,唱了一首没人听过的谣曲……醒来后,全村人都做了同样的梦。于是我们来了。”
豆芽怔住。她忽然明白,那场“无名大会”点燃的不只是人心,更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语灵”??那些曾因谎言太久而沉寂的语言之魂,正在借万物发声。贝壳、枯木、石缝中的苔藓,甚至死者的墓碑,都成了真语的载体。
消息如野火燎原。半月之内,又有三十六支队伍陆续抵达山谷。有人带来被焚毁的家谱残页,上面用血写着祖辈参与镇压起义的罪行;有人献上母亲临终录音的竹筒,里面反复念叨“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妹妹”;更有南方渔民抬来一具泡发的尸体,颈间挂着一枚刻满忏悔文的铜牌??那是某位高官私生子,一生隐姓埋名,死后仍愿以尸身传递真相。
豆芽下令:不立碑,不编册,不命名。所有言语皆由陶铃共振送入地脉,任其自然流转。她说:“若我们将真实也制度化,便又走上老路。”
然而,风暴终究再起。
某夜,京师方向突现异象:天空裂开一道赤红色缝隙,宛如巨口垂涎。紧接着,一座悬浮楼阁自云中降下,通体漆黑,檐角悬挂百千铜舌,随风摆动,发出整齐划一的诵读声??正是新版《新正言录》的开篇:“言贵中和,语须有序,妄动唇舌者,心必不诚……”
“语控塔!”阿枝失声,“他们竟真的建成了!”
据沈知白早前密报,共议阁联合旧日机关术士,耗费十年心血打造此物,名为“正音中枢”,实为终极驯化装置。它能捕捉全国范围内超出标准频率的“异常语音”,并通过共鸣反向压制,使人一旦开口说违禁之语,喉头即感灼痛,久而久之,便会本能回避“错误表达”。
更可怕的是,这座塔并非孤立存在。随着它缓缓落地,东西南北四方同时升起四座副塔,形成五芒星阵型,将整个九州笼罩其中。墨脉流动明显受阻,初音井水开始浑浊,连那枚熔化后升腾的光点也在空中凝滞不动。
“他们在重建语言秩序。”豆芽望着天际黑影,声音冷如寒铁,“这一次,不是靠恐惧,而是靠‘舒适’。他们会告诉你:这样说话更优雅,更和谐,更适合太平盛世。”
果然,数日后各地传来消息:百姓渐渐不愿多言。不是不敢,而是“懒得”。官方发放“雅言手册”,教授“得体谈吐”,茶馆酒肆流行起一种新型吟唱,旋律优美,内容空洞,人人哼唱却无人记得歌词。孩子们在学校学会的第一句话不再是“我是谁”,而是“我该如何被喜欢地表达自己”。
一场无声的清洗正在进行。
豆芽知道,若放任不管,不出三年,人们将彻底丧失说“不舒服的话”的能力。那种源于痛苦、羞耻、愤怒的真实,会被视为粗鄙、失礼、不合群。真语将不再需要被禁止,因为它已无人愿说。
她召集所有留驻山谷的旅人,宣布一项计划:**逆语行动**。
“我们要制造一场‘语言瘟疫’。”她说,“让混乱、矛盾、不合逻辑、令人难堪的真话,像病毒一样传播。”
具体做法极为冒险:挑选一百零八名志愿者,每人携带一段极端真实的个人秘密,深入各大城市,在人群密集处当众说出。不论后果如何,不得辩解,不得逃离,只许说完即走。目的是打破“说话必须有意义、有目的、有分寸”的潜规则,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哪怕一句话毫无价值,只要它是真的,就有存在的权利**。
第一批三十人出发当日,天降暴雨。豆芽站在山崖边,看着他们消失在雾中,手中紧握小满留下的最后一支透明陶笛。那是用初生婴儿啼哭时震动的第一缕空气凝结而成,吹响一次,便耗尽一生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