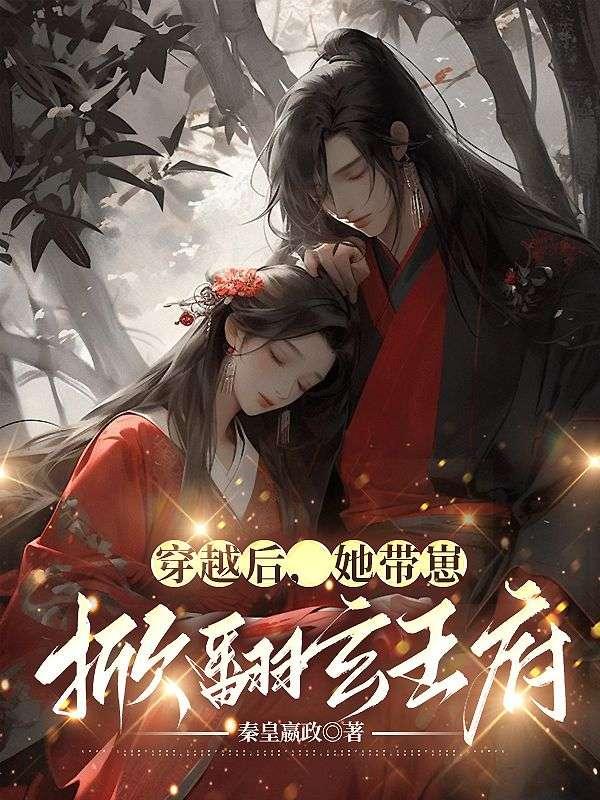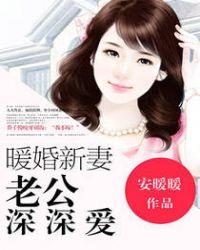宝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48章 真是个傻子这都信(第3页)
第1948章 真是个傻子这都信(第3页)
>“凡人皆有责护弱小,非因力所能及,乃因心不能忍!”
歌声穿云裂月,惊起江畔群鹭。
而在西北,沈知白正跪在雪地中,为一名垂死老妇盖上最后一条棉被。粮尽已三日,他撕碎自己的衣袍,煮成糊汤分食。孩子们围在他身边,嘴唇发紫,却仍齐声背诵:
>“我也想做一个好人。”
忽然,远方传来驼铃声。
一队商旅踏雪而来,为首者竟是归南铁匠李大郎,身后五十辆牛车满载米粮棉衣,旌旗上书:“民间义援,千里不辞。”
沈知白热泪纵横,扑跪雪地。
李大郎扶起他,笑道:“张老先生说,朝廷拦得住官道,拦不住人心。这一车车,全是百姓偷偷塞进香客包袱、僧人化缘袋、戏班行头里的。”
当夜,篝火燃起。
沈知白取出沙盘,命孩子们重新写字。这一次,他们写的是:
>“谢谢。”
风依旧猛,沙依旧冷,但人心已暖。
归南书院,文察使终于退去。
并非因妥协,而是因无力。
短短半月,全国各地竟涌现数千起“民间讲书”:渔夫在船头说《守望录》,村姑在织机旁唱《守望录》,甚至连街头算命瞎子,也改口讲“一善遮百丑”的段子。更有甚者,某县县令发现自家五岁幼子睡前必诵“爱人者人恒爱之”,追问之下,竟是奶妈所教。
赵使愤而上奏,反被御史弹劾“扰民过甚,激变舆情”。皇帝览奏,久久不语,终提笔批曰:
>“民心所向,如水东流。堵之则溃,导之则润。准其存续,但令修订,勿涉朝政。”
圣旨再下,文察使撤回,义行司保全,《守望录》正式列为“民间劝善典籍”,允在私塾传习。
捷报传至书院那日,正值春分。
张砚生率众登后山,于乌木杖旁再植一株蓝花铃草。小满亦至,手中捧着那方绣名布帕。
“先生,”她轻声问,“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能不能也种一棵?”
张砚生望着她,缓缓道:“不必等那一天。只要你还在唱,就永远活着。”
他转身,面向山谷,朗声道:
>“今日起,守望书院不再设墙。
>讲堂开于田间,课本写在墙上,
>教师是每一个愿说善的人,
>学生是每一个愿听善的心。
>从此,天下皆书院,万人共执灯。”
话音落下,风铃骤响。
一声,两声,千声万声,自山谷、城镇、渡口、荒原,遥遥呼应。
而在遥远的北方边关,一名戍卒在哨塔上写下家书:
>“爹,我今日教同袍认字,第一句是‘我也想做一个好人’。
>他说,这话说着说着,心里就不冷了。”
春风拂过大地,残雪消融。
新芽破土,万物复苏。
有些光,始于一盏灯。
而有些灯,终将照亮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