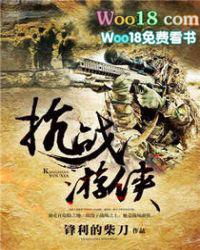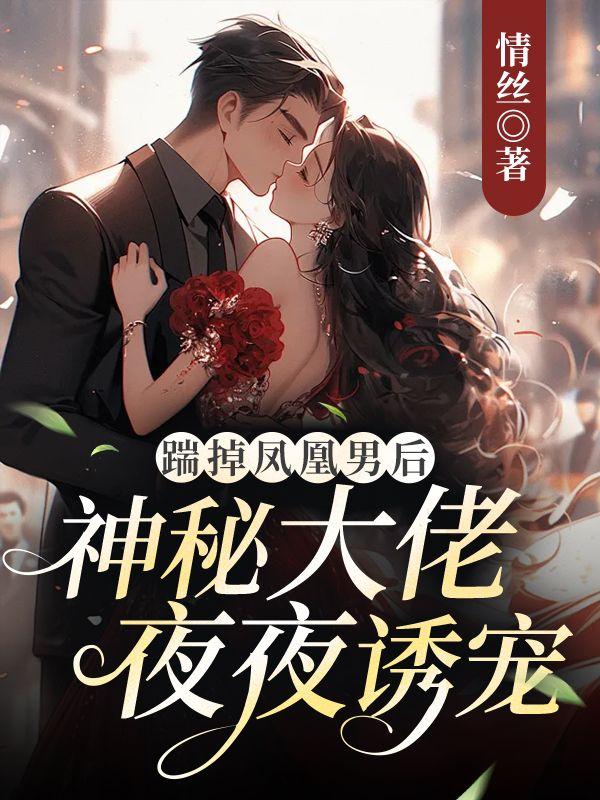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青葫剑仙 > 第两千五百四十四章 逆天行(第1页)
第两千五百四十四章 逆天行(第1页)
梁言瞳孔骤然收缩!
这一指之威,远超之前遭遇的任何攻击,竟让他久违地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指劲未至,那恐怖的威压已碾得他周身骨骼咯咯作响,护体灵光如风中残烛般明灭不定。
“骸骨巨猿……。。。
风过山林,草木低语。那片忆剑草在窗台停留片刻,便被孩童无意拂落,飘入泥泞小径,又被一阵急雨冲刷进溪流。溪水潺潺,载着它顺流而下,穿村越野,最终汇入大江。沿途所经之处,竟有无数微光自两岸升起??那是家家户户油灯未熄的窗棂,是夜归人手中摇曳的纸灯笼,是老妪在灶前低声念叨的亡夫乳名,是少年伏案抄写《愿海纪事》时滴落在纸上的汗珠。
江流奔涌,不问归途。而青年已再度启程,背影融入晨雾,如一缕青烟散于天地之间。
他行至中原与南疆交界的一座古渡口,正值梅雨连绵。江面烟波浩渺,舟子撑篙而歌:“逝水无回路,孤帆逐岁寒。谁记当年勇?唯有芦花残。”歌声苍凉,却在唱到“谁记当年勇”一句时骤然卡顿,仿佛记忆断片。舟子挠头苦笑:“怪了,这调子我唱了几十年,怎么今儿总觉得漏了两句?”
青年立于岸边,静静听着。忽见江心漩涡乍起,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链自水底浮出,缠绕在一艘沉船残骸之上。那船身刻有“义济号”三字,早已模糊不清。他闭目凝神,胸口日记微微发烫,一段尘封往事如潮涌来??
百年前,此船曾满载灾民渡江避难。彼时疫病横行,官府下令封锁河道,凡带疫者不得过江。船主乃一介布衣商贾,名唤林守仁,闻讯后毅然决裂契约,私自开船救人。途中遭官兵围剿,炮火击沉其船。临没之际,他将一本记录灾民姓名与去向的册子封入铜匣,投入江心,并高呼:“纵我不存,亦须有人知他们曾活过!”
此后百年,江底冤魂不散,每逢阴雨,便有哭声随波传来。渔人惧之,称此为“哑魂滩”。而今日,因青年心念共鸣,源井记忆牵引,那铜匣终于破泥而出,附着于铁链之上,缓缓升至水面。
青年脱鞋涉水,取匣开锁。内中册页虽经百年浸蚀,墨迹竟未全消。他逐一辨认,将幸存者后裔之名默记于心。当夜,他在渡口搭起草棚,燃起篝火,执笔誊录,直至天明。翌日清晨,十余位村民自发前来围观,其中竟有一人颤声惊呼:“这是我太爷爷的名字!祖上传说他曾乘船逃难,但没人知道结局……原来他活下来了!”
消息如风传开。短短月余,三百余名后人寻根至此,跪拜江岸,焚香祭奠。更有匠人提议铸碑立传,将所有名字镌刻其上。青年未阻亦未助,只在碑文起草时悄然留下一行小字:
>“非为扬名,但求不亡。
>一念记得,万劫不空。”
碑成那夜,江雾弥漫,忽有千百点幽蓝萤火自水底升起,环绕石碑飞舞三周,而后汇成一条光路,直指南方群山。众人屏息凝望,只见远处山巅似有一座虚影庙宇浮现,门匾上书“忆归祠”三字,转瞬即逝。
自此,“义济碑”成为民间朝圣之所。每年清明,无数人携酒食前来祭拜无名英魂。而那本誊录的册子,则由一位退休教书先生保管,每日清晨诵读一遍,声传十里。
青年悄然离去,足迹踏向西南边陲。
此处崇山峻岭,瘴气弥漫,村寨散落云雾之间。他途经一处苗寨,正逢三年一度的“失语节”。寨中长老告诉他,百年前曾有巫女预言:若族人遗忘母语七代,山神将收回赐予的良田与清泉。如今第六代孩童已多不说苗话,仅用官话交流,故全寨举行仪式,祈求宽恕。
青年走入祭坛,见中央石台上摆放着一面铜鼓,鼓面布满裂痕,据说是祖先迁徙途中所携,能通天地之声。然而近十年来,无论怎样敲击,皆无声响。
他伸手轻抚鼓面,指尖触及之处,裂纹竟泛起淡淡青光。刹那间,脑海浮现一幕画面:百年前那位巫女并非预言灾难,而是预见了今日之遗忘。她曾在临终前写下一部《古音谱》,藏于寨后溶洞深处,以血为墨,以骨为笔,盼后人重拾语言之根。
青年入洞寻觅三日,终在钟乳石后找到一方石棺。棺中并无尸骨,唯有一卷羊皮卷轴静静安放。展开一看,竟是用古老苗文与象形符号交织而成的语音图谱,记载着从婴儿啼哭到祭祀祷词的全部发音体系。更令人震惊的是,每一页边缘都密密麻麻写着批注,字迹熟悉??正是他自己前世的手笔。
“原来我也曾是这里的孩子。”他喃喃道。
他留寨半年,白日教童蒙习《古音谱》,夜晚则以青葫清露滴于铜鼓裂缝之中。第七个满月之夜,鼓声突响,浑厚悠远,震动群山。整座寨子的人同时梦回童年,听见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父亲讲述的创世神话,祖母低语的禁忌箴言……醒来后,人人开口皆复述母语,流畅如初。
寨老含泪叩首:“你不是外人,你是我们丢了百年的‘言归者’。”
青年摇头:“我只是路过的人。真正的‘言归者’,是你们自己。”
离寨那日,全村送至山口。一个五岁女童追上来,塞给他一只手工编织的草铃铛,认真地说:“等你说完所有故事,就摇它一下,我们会听见的。”
他收下铃铛,挂在腰间。从此行走世间,再无声响,却总觉耳边回荡稚嫩呼唤。
数月后,他抵达东海之滨一座荒岛。传说此地曾是流放文人的绝境,如今只剩断壁残垣,野藤缠楼。岛上唯一居民是个疯癫老渔夫,终日对着大海吼诗,诗句颠三倒四,无人能解。
青年登岛当晚,便坐在礁石上听老人吟诵。起初只觉混乱,但随着体内灵力运转,竟渐渐理出脉络??那些看似错乱的句子,实则是一首长达三千行的史诗残篇,名为《囚心赋》。作者正是百年前因直言进谏而被贬至此的大学士沈砚之。他在孤岛上耗尽心血写下此作,却被朝廷派兵焚毁原稿,仅靠口耳相传留存片段。可惜传诵者或死或忘,终致支离破碎。
青年每夜记录老人呓语,以日记本为引,唤醒源井中残存的记忆烙印,逐句补全缺失章节。某夜风雨大作,他正写至“宁以寸舌抗雷霆,不使丹心化寒灰”一句时,忽然狂风掀浪,海中浮现出半截石碑,上面赫然刻着接下来的四句:
>“骨埋沙砾犹作砥,魂栖浪涛亦为堤。
>若有一人读我字,便是春风渡死地。”
碑文显现不过片刻,旋即沉没。但青年已牢牢记住。
七七四十九日后,《囚心赋》终得完整。他将全文刻于岛中央巨岩之上,又以青葫之力激发文字灵性,使其夜夜散发微光,宛如星辰铺地。自此,每当月圆,海上过往船只皆可见此奇景,船员们纷纷传颂,称其为“海上诗狱”。
不久之后,mainland上掀起一股私抄禁书热潮。许多人家暗中收集被官方删改的历史文献,甚至冒险重印《囚心赋》。官府震怒,屡次搜查,却发现这些抄本无论烧毁多少次,第二日总会在城门口、学堂墙、寺庙香炉中重新出现,仿佛文字本身具有生命。
与此同时,皇宫内院也起了波澜。一名老太监深夜整理先帝遗物时,在一幅山水画夹层中发现一封密信,竟是当年下令焚书的皇帝亲笔悔书:“朕毁真言,罪莫大焉。若有后人续之,乃国之幸也。”他颤抖着将信抄录十七份,分别藏于各地佛像腹中、古塔砖缝、书院梁柱,只待有缘人发现。
青年不知宫闱风云,只继续他的旅程。
这一日,他来到西北戈壁,遇见一支商队被困沙暴。救援之后,首领拿出一块奇特玉佩答谢,说是祖上传下,据称能照见人心最深的记忆。青年接过一看,玉佩中央竟嵌着一小片忆剑草干叶,与他当初所得如出一辙。
“这是我们‘忆行商帮’的信物。”首领解释道,“三百年前,有位游方道士赠予先祖此物,说只要代代护送记忆前行,哪怕身处沙漠,也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走南闯北,替人捎带家书、传递遗嘱、运送孤本典籍……虽为商人,却不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