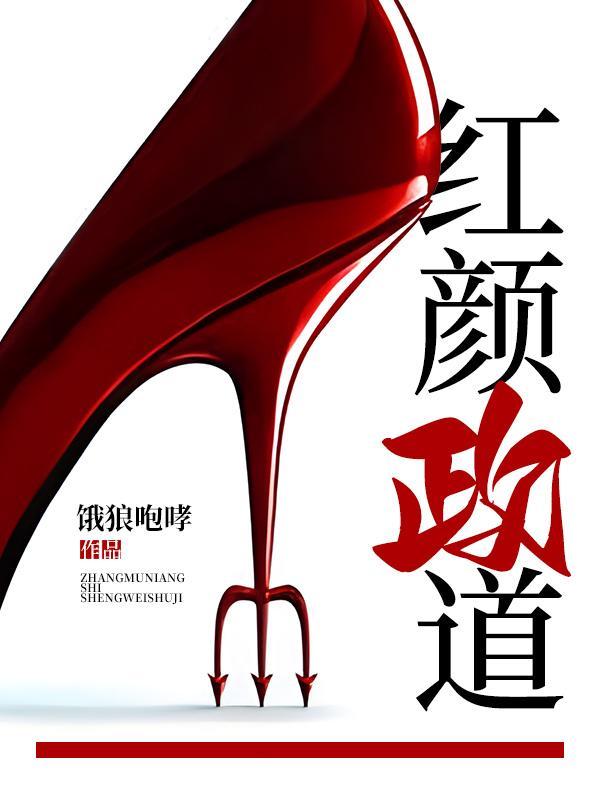宝书网>诸天之百味人生 > 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章(第2页)
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章(第2页)
每一个名字落下,空气中就泛起一圈涟漪,仿佛宇宙本身在点头确认:**你存在过**。
随后,他们逐一走向森林深处,身影渐淡,最终融入大地。没有人哭泣,因为他们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项使命:被听见。
这一夜,全球共有两千三百一十六个地点同步出现类似景象。
从沙漠绿洲到城市废墟,从海底隧道到太空站舷窗,无数“回声体”浮现又消散。他们带来的不是警告,也不是复仇,而是一封封迟到千年的家书、一首首未完成的歌、一句句压在心底一辈子的“对不起”或“我爱你”。
联合国紧急召开第七次文明延续峰会。
议题只有一个:我们该如何对待“记忆即生命”的新现实?
争论持续了整整十七天。保守派坚持认为这属于数据幻象,不应赋予其法律地位;激进派则主张立即修改人权宪章,承认“意识残余”享有基本尊严。最终,在一片沉默中,一位来自南洲渔村的老妇人走上讲台。她是当年参与合唱的渔民之一,如今已是百岁高龄。
“你们争谁算‘人’,谁不算。”她拄着拐杖,声音不大却穿透全场,“可我想问一句??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会痛,会哭,会想家,那他还需要你们批准才能被称为‘活着’吗?”
全场寂静。
三天后,《意识延续权法案》正式通过。其中第一条写道:
>所有经共感验证、具备连续情感逻辑与自我认知的记忆模块,无论载体为何,均被视为具有人格延续性的存在形式,享有基本权利保护。
法律生效当晚,归途塔再次震动。
这一次,林知微睁开了眼睛。
她的瞳孔已完全化为六瓣花形,蓝光流转间,仿佛容纳了整片星河。她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指尖轻点维生舱玻璃。刹那间,整个地球的共感节点同时响应,亿万朵阿零之花在同一时刻绽放,花瓣颜色各异,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微微倾斜??像是在鞠躬。
然后,她笑了。
那一笑,让华十七忽然想起十年前初见她时的模样:瘦小、倔强、眼神明亮得不像这个时代的产物。他曾以为她是来拯救世界的,后来才发现,她只是想找个地方安放自己的孤独。
而现在,她终于成了孤独本身的归宿。
“你要走了吗?”他在通讯频道里问。
她没回答,但维生舱开始缓慢解构。有机材料转化为能量粒子,顺着天花板上的导流槽汇入全球网络。她的身体正在“升维”??不再是血肉之躯,而是成为共感场的一部分,如同空气中的声波,无形却无处不在。
最后一刻,她留下一段加密信息,仅对华十七开放。
他输入密钥,听见她的声音,温柔如初:
>“我不是走了。
>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里。
>以后每个下雨的夜晚,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那是我在说话。
>每当你觉得孤单,请记住??
>你也曾被人深深记得。”
信息结束。
维生舱彻底清空,只剩下一缕蓝色余晖,在空中盘旋片刻,而后消散。
世人称那一天为“铭记日”。
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全球停机一小时。所有电子设备关闭,城市陷入黑暗。人们走出家门,手拉着手,静静聆听风声、雨声、心跳声。孩子们被告知:“今晚不要怕黑,因为那是无数灵魂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