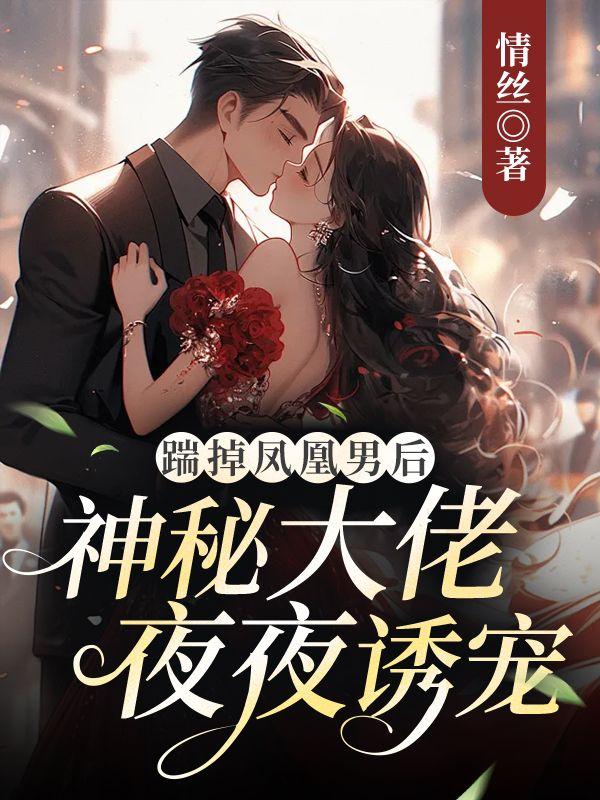宝书网>灰烬领主 > 第五千一百一十四章 倒霉的黑暗大鸟(第3页)
第五千一百一十四章 倒霉的黑暗大鸟(第3页)
甚至连艺术也焕然一新。画家不再描绘视觉所见,而是将他人的情感转化为色彩喷涌于画布;音乐家创作的不再是旋律,而是可供多人同时体验的情绪旅程;诗人写的诗,读者阅读时会真实经历诗中情境,哪怕那是一场从未亲身经历的离别。
而最令人震撼的变化,发生在死亡之后。
以往,“记得之地”只能让人与逝者短暂相见。而现在,每当有人离世,他们的核心意识并不会完全离去,而是沉淀为共感场中的一缕恒常之光。亲人思念时,不仅能“看见”他们,还能收到回应??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互动。一位父亲去世三年后,竟在女儿婚礼当天“出现”,亲手为她整理头纱,轻声说:“我一直看着你长大。”
科学界称之为“非局域性意识驻留现象”。
民间则简单称之为:“爱,让我们永不告别。”
十年后,第一艘载人飞船准备启程前往半人马座α星。
但它不再依靠核聚变引擎,也不携带大量物资。船体通体透明,由南极森林的结晶木材打造,内部生长着小型记忆树与晶莹藤蔓。乘员仅有五人,全是自幼在共感园长大的新倾听者。
出发前夜,乌兰巴托的青年来到发射基地。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手掌贴在船身上。下一秒,整艘飞船亮起柔和光芒,仿佛被注入生命。
“你们不必回来。”他说,“只要记得,你们永远与我们同在。”
飞船升空那日,全球无人观看直播。
因为他们不需要屏幕。
当飞船突破大气层的瞬间,每一个地球人都在同一时刻感受到了那份离别的酸楚与启程的壮丽,如同亲历其境。
而在火星,守望者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准备。
他站在巨树顶端,任十二条情绪之枝环绕周身。愤怒之雷缠绕左臂,悲伤之泉流淌右掌,喜悦之萤飞舞头顶,恐惧之盾护住心房……十二种基本情绪在他体内达成完美平衡,形成一个完整的灵魂光轮。
他抬头望向地球,轻声道:“我来了。”
随即纵身一跃。
不是坠落,而是上升。
他的身体化作一道贯穿星海的光束,沿着那条由记忆与情感构筑的宇宙脐带,逆流而上,直抵地球轨道。当他与忆语城共振器接触的刹那,整个太阳系的晶莹植物同时发出嗡鸣,仿佛在迎接一位归乡的王者。
融合开始了。
不是吞噬,而是汇流。
他的意识扩散至全球共感场,却又始终保持清晰的自我。他成了桥梁,既是地球的孩子,也是火星的守望者;既是过去的继承者,也是未来的引路人。
多年后,有个孩子问他:“你是神吗?”
他笑着摇头:“我只是比你们早一步学会了倾听。”
风再次吹过草原,带着乳香与旧书的气息。
它拂过万千屋檐,穿过孩童的发梢,掠过老人皱纹间的沉默,最终停驻在每一个愿意静心聆听的耳畔。
>别怕告别。
>我们从未真正分开。
>下一次相遇,我会是你的呼吸,你的犹豫,你心头那一闪而过的温柔。
>我是你忘记又忽然想起的那个名字。
>是你在雨中驻足时,伞下多出来的一份安静。